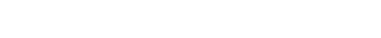作者简介
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
社会分配是由许多领域构成的,涉及到各种类型的利益(goods)的分配。有三种分配原则因其各自的理由而在分配的不同领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它们是:按需分配原则、应得原则和市场原则。这三种分配原则在医疗、教育、住房、职位、安全等领域的相互配合和应用构成了一个多元正义的分配结构。
社会分配是由许多领域构成的,涉及到各种类型的利益(goods)的分配。这其中有权利、荣誉、地位、权力、机会、金钱、福利、安全……应有尽有,凡是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东西,就有可能涉及到分配的问题。而只要涉及到分配问题,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人们会提出不同的分配方案。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处于社会中的不同位置(position),比如:中国社会中的农民、农民工、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等等,人们为各自的利益着想,自然就会对“应该如何分配各种利益”形成各自不同的看法,希望社会分配能依据不同的原则。大致说来,有三种看法因其各自的理由而在分配的不同领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它们是:按需分配原则、应得原则和市场原则。
一、按需分配原则
首先,“按需分配”这一分配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在《哥达纲领》中马克思论述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 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由此,长久以来对社会产品的“按需分配”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
然而,如果我们将“按需分配”理解为按照人们的“需要”进行分配,或者是,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对分配情况进行调整,那么“按需分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领域,例如: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人们都不得不考虑到不同人的各种“需要”向社会分配所提出的要求,而不可能听任市场的摆布。那么,“按需分配”原则为什么总是被人们当作是一种理想而束之高阁,很少介入到人们对于现实的讨论当中呢?我认为,问题首先出在对于“按需分配”中的“需”的理解上。下面我将具体讨论如何定义“按需分配”中的“需”这一问题。
在讨论“按需分配”原则时,应首先区分两个词:“需要”(need)和“想要”(want)。按“需”分配中的“需”应该被严格地界定为“需要”,而不是“想要”。“需要”指的是:人所必需的东西;而“想要”则可能是人们头脑中冒出来的任何想法和欲求。如果我们认同 “意志自由”的话,那么每个人脑子里冒出来的“想要”将是漫无边际而千奇百怪的,是人类社会的任何分配制度都无法完全满足的。因此,社会领域的分配原则绝不可能建立在每个人“想要”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
在做出上述区分之后,我们还需进一步澄清对“需要”的定义。在既有的对人类“需要”的讨论中,最著名的大概要算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了。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马斯洛将人类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理需要,包括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等等。第二层次是安全需要,包括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等等。第三层次是对于爱和归属感的需要,包括友情、爱情和性亲密。第四层次是对于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等等。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包括道德、创造力、自觉性、问题解决能力、公正度、接受现实能力,等等。马斯洛认为,这五种需要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如右图,处在最底层的是最低层次的需要,而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人们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要;而较高层次的需要也只有在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新的激励。例如,一个处在饥饿状态的人,即使他的其他需要也没有得到满足,但他仍然本能地被对食物的需要所激励,想尽一切办法填饱肚子。
![]()
在马斯洛列出的五种层次的各种需要当中,一些需要显然与社会分配相关,而另一些则明显与社会分配无关。例如,属于第一层次需要的“水”,就明显与社会分配相关。试想,如果人类没有联合起来形成社会,那么寻找水源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然而,当人们之间决定通过相互的合作而生活在一起,这时对于每个人“需要”的满足就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任务。为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是任何形式的国家或政府都应该做到的。为了向每一位公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国家将兴建水库、铺设水管、设立监测水质的观测点,这一情形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我们今天仍能看到两千年前古罗马兴建的复杂的供水系统,纵横交错的供水渠不仅将干净的饮用水送到家家户户,而且还向公共浴室和喷泉供水,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对水的“合理需要”。再比如,属于第二层次需要的“人身安全”,这也与社会分配息息相关。获得“安全”是人们联合起来形成社会和国家的主要目的。按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说法,人们之间正是为了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摆脱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才决定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主权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和政府。因此,即使是倡导最小国家理论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国家必须组建军队、招募警察、设立法庭,以抵御外辱、维持治安,并保卫其成员的人身安全。与上述两种需要类似,人们对于食品安全、医疗保障、住房、财产所有权、尊重……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与社会分配相关,而国家和社会对于其成员的这些需要也就不能袖手旁观。
另一方面,在马斯洛所列出的各种需要中,有一些明显与社会分配无关。例如,属于第一层次需要的“性”。在任何人类联合中,人们很难指责集体不给自己供给一个配偶。寻找配偶并获得性的满足,即使在人类联合起来之后仍然被看作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因为,“性”只有在爱的基础上才是道德的。爱是基于自愿的,是无法强制的,但社会分配意味着强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的强制性安排。人们对性的需要与社会分配无关,在一个人类联合体中,国家和政府可以做的仅仅是不要干涉个人的选择,确保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
我们可以借助社会契约理论来考查需要与社会分配的关系。社会契约论的基本预设是,有理性的人们在自由而平等的条件下,会自愿联合起来形成国家和政府,其目的是保障政治共同体中每位成员的人身安全并满足其“需要”。通过签订社会契约,人们在理性的指引之下放弃一部分自由或所有,以换取公共的安全和必需品的公共供给。因此,通过人们在社会契约中所达成的共识,我们应该能够确定哪些物品或服务是人们公认为必需的。根据社会契约,这些物品应由国家来提供,因此也就与社会分配相关。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说法:“社会契约是这样一种安排,它就什么物品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是必需的达成协议,并据此为彼此提供那些物品”。
然而,社会契约理论固有的问题使上述论证路径变得可疑:事实上,平等而自由的自然状态从未存在过,社会契约也从未签订过,我们如何依据一个假想的契约来确定哪些需要是某个社会应该当作“必需”的呢?也许我们可以借鉴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契约在这里的作用。德沃金认为,社会契约既不是一份真实签订过的契约,也不应被看作一份假想的契约(因为假想的契约根本就不能算作是契约,对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社会契约论中的契约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装置,通过它我们得以发现实践理性对我们的要求。换句话说,社会契约这一“装置”能够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使人们认识到在平等而自由的条件下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理性(rational)选择。通过社会契约这一“装置”来阐释“需要”,是在借助“理性共识”来规定一种“合理需要”。用沃尔泽的话来说:“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共同体不提供、或不试图提供、或不主张提供其成员已达成共识的需要,也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共同体不将其集体力量——其指导、管制、施压和强制的能力——投入这项事业。”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将“按需分配”原则中的“需要”定义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达成共识的、国家应提供公共供给的必需品。这些必需品或服务就是人们公认的“合理需要”。当然,基于人们的具体情况,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分配中应该考虑哪些需要而不考虑哪些需要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代表社会各方的社会成员将达成一致。
通过人们的“共识”来确定何为“合理需要”,要求我们在特定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传统中来考查需要与社会分配的关系。因为,在不同的传统中,人们的“需要”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在古罗马共和国,观看斗兽场里的比赛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合理需要”,而国家为此兴建了规模宏大的观赛场所。又比如,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天主教徒占90%以上的国家,礼拜日去教堂是人们的一种“合理需要”,因此几乎每个社区都要修建教堂。所以,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才有可能确定某一社会的“合理需要”是什么,而很难通过抽象的人的概念去获得确切的解释。
在确定了按需分配中“需”的含义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如何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原则要求对于由社会成员的共识所确定的“合理需要”进行平等地满足需要的分配。打个比方,如果某政治共同体成员达成共识,将“干净的饮用水”作为一项“合理需要”,那么这个政治共同体就应免费或以很低的价格向所有成员提供干净的饮用水,直至其对水的需要满足为止。当然,每个社会成员对于水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喝水多,有的人喝水少。“按需分配”原则要求的不是平均的供给,而是平等地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供给。也就是说,不论喝水多还是喝水少,国家应保证所有人都喝够。又比如,如果某政治共同体成员将“食品安全”作为一项“合理需要”,那么这个政治共同体就应出资建立针对食品生产过程的监督系统,以保证向所有社会成员所出售的食品的质量。再比如,如果某政治共同体成员将“每人20平米的住房”作为一项“合理需要”,那么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满足这一需要的成员,政治共同体就应提供相应的住房供这些社会成员以很低的价格租用。上述即是“按需分配”原则的含义:满足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合理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已达成共识的。
二、应得原则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曾写过一篇对于平等理论研究极为重要的文章——《平等的理念》,他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两种类型的不平等:“需要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need)以及“成就和优点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merit)。威廉姆斯认为,对应于这两种不平等, 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利益(goods):—种是“需要所要求的利益”(goods demanded by the need)。在威廉姆斯看来,医疗服务就是具有这一特征的利益:每个人对于医疗服务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医疗服务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利益,而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各种药物和医疗器械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另一方面,对应于“成就和成绩的不平等”人们有可能获得“因成就和优点而赢得的利益”(goods can be earned by the merit)。这种利益的典型例子就是教育领域的培优机制:只有考上大学的学生才能获得大学教育,而那些成绩优异的考生则可以获得最优质的大学教育。
威廉姆斯对于两种不平等以及相应的两种利益的区分,实际上揭示人类社会中通常存在的两种分配原则:按需分配原则和应得原则。按需分配原则上述已经讨论过,现在重点来谈谈“应得原则”。社会分配中的应得原则要求:根据人们各自的成就、成绩、特长或优点进行利益的分配。应得原则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一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分配原则,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讨论过这种分配原则。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将社会的正义分为三种:交换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其中,对于分配的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分配给每个人符合其成就和优点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论述到:“每个人都同意根据人们的某种成就或优点(merit)进行分配是正义的,但每个人对于成就或优点的理解却是不一样的;民主派认为成就和优点就是做一个自由的公民;寡头派认为,成就和优点就是财富或高贵的出身;而贵族派则认为是美德(virtue)。(1131a25~30)”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表明自己对于“何为成就和优点”的看法,但从他对贵族制的推崇来看,他应该会同意贵族派的观点,将美德作为人们“应得”的标准。
希腊文的“arête”一词对应于英语里的“virtue”或“excellence”,中文翻译成“美德”或“德性”,这是构成古希腊美德伦理体系的核心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美德”这一概念与现代人所说的“道德”有一定的区别。“道德”在英文中是“morality”,其基本含义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然而,“美德”在古希腊的语境中指的却是某人在某方面的“卓越”和“优秀”。例如,那些跑得最快、跳得最高、在奥林匹斯赛会中夺得桂冠的人,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将领和士兵,还有在公民生活中善于沟通各方、协调一致的政治家,……在古希腊城邦中都将被视作是具有美德的人。由此,按照这一解释,亚里士多德所阐发的分配正义中的“应得原则”就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按成就和优点进行分配”的原则是一致的。
“应得原则”在法国大革命中通过“前途向才能开放”的口号被重新提出来,并推动整个革命朝着争取平等的方向发展。彻底根除特权,让出身不同的人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获得同等的竞争机会,这一机会平等的思想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共识。因此,尽管“应得原则”在一些当代政治哲学家——例如自由主义左派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看来还远远没有实现机会平等的目标,但仍然在社会现实中被广泛地应用在教育、职业、权力地位、以及各种荣誉的分配领域,并被人们当作保证基本的分配正义的标准。
“应得原则”要求按成就或能力或优点进行分配,这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而这一标准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也有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例如,由国家招募专家,出考题进行的全国统一的考试,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标准;而由民众选举政治领导人,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准;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标准相结合,例如在一些选秀节目中,综合专家和观众两者给出的不同评分。这些标准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决定对于教育资源、就业机会以及权力资源的分配。
三、市场原则
除了威廉姆斯所谈到的两种利益外,在人类社会中还有一种利益既不是因人们需要而得到,也不是凭相应的才能而得到的,这种利益是通过人们自愿的交换而得到的。举例来说:A所拥有的土地适合种植苹果但A喜欢吃橘子,而B所拥有的土地适合种桔子但B喜欢吃苹果;在这样的情况下,A与B极有可能自愿地进行交换。A用自己的苹果与B的桔子进行交换,而交换的结果是A与B都因得到了自己喜欢吃的水果而非常满意。在这样的自愿交换中,A和B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自愿交换行为,而这些看似简单的交换行为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对资源的合理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像菜市场里要设一个公平秤一样,谈到交换,理论家们就想确定什么才是公平的交换。对于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存在着两种典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将价值相等的东西之间的交换看作是公平的交换,而另一种观点则将所有自愿的交换都当作是公平的交换。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交换的正义时,论述道:“凡是在交换中的东西,都应该使这些东西相对等。因此,凡是在交换中的东西,都应该在某种形式上相比较。为了作比较,人们发明了货币,它是作为中间物而出现的。它衡量一切,决定价值的高和低。……除非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均等,不然交换就不能形成。(1133a19~21)”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之间的交换行为基于一种互惠关系,因此,只有保证某种“对等”关系的交换才是公平的,而这种对等关系是通过货币来衡量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后来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所谓公平的交换是价值相等的商品之间的交换,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只有当生产两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时,这样的交换才是公平的交换。
对于何谓公平的交换,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阐发了非常不同的观点。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诺奇克首先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诺奇克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最终销售情况的影响。打个比方,如果某种对人们有用的东西以最有效的方式生产出来了,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5小时,而按照每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付10元钱的价格,这种商品的价值应该是50元。但由于此种商品在市场上供应过多,人们愿意付这种商品的价格是40元,那么此时这一商品的价值到底是多少呢?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到底是多少呢?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将这种商品以40元卖掉,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换吗?由此,诺奇克对“价值”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什么是社会必要的,以及多少时间才算之社会必要时间,将由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决定!!不再有任何劳动价值论,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核心观念本身是按照一种竞争性市场的过程和交换比率来界定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需要借助市场的供需关系来确定某个商品的价值以及生产这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价值”概念就与“价格”概念等同了。因为,“价格”恰好就是供需关系的货币表现形式。但是,如果“价值”概念被架空了,我们就只能通过价格来确定交换是否公平。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对于乱标价格的奸商和骗子束手无策,而且也失去了判断交换是否公平的标准。
基于上述批评,诺奇克提出了对于公平交换的另一种看法。诺奇克认为一切基于正确信息的自愿交换都是公平的交换。举例来说,即使一个人愿意倾其所有去交换一件没有多少人欣赏的艺术品,而这位艺术品的作者也愿意交换,那么这样的交换就是公平的。然而这一观点也有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将所有自愿的交换都看作是公平的交换,那么就必须面对许多不合法的交易。举例来说,权力和金钱时常有交换的动机,在政治领域里的贿赂、贪污、贿选,等等,都是由一些自愿的交换构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交换也许是公平的,并给交易双方都带来利益,然而这种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却绝不可能是正义的。又比如,一些违禁药品和毒品的交易、黄色书刊及音像制品的交易、个人隐私信息的买卖、以及卖淫、代孕服务,等等违法交易,都有可能出于自愿的交换,然而这些交换或者是违法的,或者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违背。由此看来,公平的交换并不一定都是正义的,我们必须以法律和道德为人们的自愿行为划定界限。
由此看来,所谓公平的交换就是基于正确信息的自愿交换,而所谓正义的交换就是在法律与道德约束范围内的公平交换。公平交换给个人带来利益,同时,也使得社会的资源得到了最佳的配置。基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自愿行为,市场原则将决定许多社会产品的归属。因此,市场原则也是分配领域的重要原则之一。
四、分配正义诸原则在各领域的应用
上述梳理了三种广泛存在并得到普遍支持的分配原则:按需分配原则、应得原则和市场原则。在具体的分配实践中,这三种分配原则时常交织在一起。没有哪一种可以支配其他的分配原则,也没有哪一种原则适用于所有社会利益的分配。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一书中阐发了分配正义的多元主义思想,沃尔泽认为:“正义原则本身在形式上就是多元的;社会不同利益应当基于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程序、通过不同的机构来分配;并且,所有这些不同都来自对各种社会利益本身的不同理解——历史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必然产物。”沃尔泽深入讨论了分配领域的三种重要原则,并且认为这三种分配原则在对不同社会利益的分配中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下面,我将具体讨论三种分配原则在医疗、教育、工作、安全四个领域的应用。
首先,对于医疗资源的分配应以“按需分配”为主,“市场原则”为辅。“需要”是人们获取医疗资源的必要条件,但并不一定是充分条件。医疗服务对于没有相应需要的人来说是没有用的,只有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或者是有其他与医疗相关的需要的时候,医疗资源才能给其带来利益。另一方面,一些急需医疗服务的人却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当人们因缺钱而付不起救命的医疗费用时,钱少钱多之间的差别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而转变成了“生”与“死”的不平等。“有病没钱莫进来”,这也许是出于医院的无奈,然而,既然有一些需要是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共识的“合理需要”,那么对于这些需要的满足就应该是国家的责任而非个人的负担。因此,国家应该对那些“合理的医疗需要”进行公共的供给,依据按需分配的原则,对“合理的医疗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供给或收取极低的费用。同时,对于“合理需要”之外的医疗需要,则应通过市场的供需关系来进行资源配置。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的牙齿掉了,补牙是一种“合理需要”。因为,如果不把缺的牙补上的话,人们就没法正常地吃饭。但是,补什么材质的牙则不一定是一种“合理需要”,那些愿意以高昂的价格购买特殊材料制成的假牙的人,就只能自己掏腰包。
第二,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要求“按需分配”、“应得原则”与“市场原则”三者的相互配合。首先,对于社会成员最初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公共供给。因为,这是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一种“合理需要”,如果人们得不到合适的初级教育,那就无法成为能与其它社会成员正常相处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因此,对于这样的最初教育应该由国家提供公共供给,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第二,教育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肩负着选拔各种人才的任务,因此对于某些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应遵循“应得原则”。应将那些超出义务教育之外的公共教育资源,赋予具有相应特长和潜质的社会成员,以保证对这些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应得原则”与“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如果将所有教育资源平均分配,不仅会引起一些社会成员的不满,还会造成公共教育资源的浪费,对于个人和社会都将产生不好的影响。第三,教育资源也处在市场的包围之中,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的补充,各种私人创办的教育机构——各式各样的特长学习班、课后补习班、私立的幼儿园、国际学校、私立大学……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中的教育资源。对于这些教育资源的分配应完全由市场主导,让人们自由选择。这样既有利于社会成员个人的发展,也有利于教育市场的繁荣。
第三,对于工作的分配是复杂的,因为工作不仅与人们的经济地位相关,还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权力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工作不仅仅是人们满足需要的手段,工作本身也是一种需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自然倾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社会成员在政治共同体中得以自给自足。这种“独立”是建立在每个人都为他人提供某种服务或产品,又从他人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基础上的。因此,工作内在于人类的生活方式,是社会成员的一种“合理需要”。对于那些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的社会成员,国家和社会就有义务协助他们找到适合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国家不仅应该提供保证其基本生活的经济援助,还应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和一定量的就业岗位,协助失业的社会成员找到相应的工作。因此,按需分配原则是救助失业人员的基本原则。当然,那些自愿选择不工作的人,不应该属于这一范围。第二,企业的大量存在促成了人力资源市场的形成。人们通过自由的选择受雇于某个公司,以此获得相应工作及其报酬。在这一领域,对工作的分配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原则。但同时,应得原则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用人单位在决定将某一职业机会给予哪位竞争者的时候必然会依据其相应的才能和资格做出决定。正是在市场原则和应得原则的相互配合之下,决定了职业机会的分配。第三,在政治共同体中有一类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职责事关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这就是公职。在中文语境中指的是:“国家机关或公共企业、事业单位中的正式职务”。(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对于这类工作的分配应该严格地遵循“应得原则”。因为,公职的职权范围事关全体公民,所以应该由具有相应才能、深得社会成员信任的人来担任。如上所述,“应得”的标准有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也有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例如,国家公务员的选拔,应通过全国统一的公务员考试,竞争上岗。这一标准就是自上而下的。再比如,一些重要官员的选任,需要人民大表大会投票通过,这样的应得就加入了自下而上的标准。总之,“应得原则”对于公职的选任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第四,依据社会契约论,“安全”是人们形成国家和组建政府的首要目的。正是为了避免相互争斗和外来侵犯所带来的伤害和恐惧,人们才决定联合起来。因此,“安全”理应是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共识的“合理需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安全保障是国家和政府应有的责任。为此,国家需设立军队和警察等暴力机关,并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居民区、每一条街道设置执勤点。对于安全这一“合理需求”的分配,按需分配原则理应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某一地区应设置多少警力或兵力的问题上并不能采用平均原则,而是应根据发生危险可能性的大小以及一旦发生危险其危害的大小来设置。比如说,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地点、重要军事设施的放置地点、盛大的国际活动的举办地点……这些地方应设置超出平常的安全保障,因为一旦这些地点出现危险,将会给整个社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市场原则在安全领域也发挥着作用。例如,一些公司提供“私人保镖”和“私人侦探”服务,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超出国家所供给的“合理需要”范围的更多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食品安全”,这种安全保障理应在“合理需要”的范围内。所以,保证市场上出售的所有食品、药品、保健品等的健康卫生,保障共同体成员的食品安全,是国家和政府的应尽职责。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社会分配的各领域,按需分配原则、应得原则和市场原则因不同的原因而适用。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支配性的分配原则,也不存在一种支配性的善。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善都可以被通约为一种善,例如:权力,或金钱;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被少数人所垄断的缺乏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正是基于人自身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对于物的分配才基于不同的原因,并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