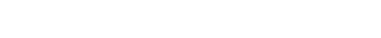毋庸置疑,稳定性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价值。如果一种政治制度不稳定,那么这一政治制度所规范的政治共同体就将陷入混乱,而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也将失去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不择手段地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陷入无穷无尽的自相残杀和相互拆台之中,而人类社会甚至有可能退回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那么,一种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使得某种政治制度所规范的政治共同体得以长治久安?对于这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罗尔斯和霍布斯的回答大相径庭。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到了他与霍布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曾指出,霍布斯把稳定性问题和政治义务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可以这样看待霍布斯的观点:强制权力是加在合作体系上的一种结构,这个合作体系失去这种结构就会不稳定。对强制权力效验的一般信仰消除着两种不稳定性。现在,友谊和互信关系,以及对于一种共同的通常有效的正义感的社会公认如何达到了同样的结果已经一目了然了。”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霍布斯那里,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根基在于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强制权力;而罗尔斯则认为,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根基在于处在这一制度之中的人们的“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本文将在呈现罗尔斯与霍布斯关于政治制度之稳定性争论的基础上,指出罗尔斯在推导出正义感时出现的循环论证问题,并讨论“正义感”和强制权力对于维护政治制度之稳定性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一、强制权力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在罗尔斯对霍布斯的契约理论的解读中,人们能走出自相残杀、相互拆台的自然状态的关键在于解决两个问题:“消除孤立”与“建立确信”。所谓“孤立”,指的是每个人都依据“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孤立地进行选择,而选择的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囚徒困境”的模型是解释“孤立”问题的最好例子。在“孤立”的状态下,两个罪犯依据“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都会做出“认罪”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完全符合“个人理性”的,因为不论对方怎么选择,选择认罪都是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然而,两个罪犯都选择“认罪”,并不是双方利益都得到最大化的“双赢”的选择,而毋宁说是一种“双输”的选择。只有当两个罪犯能够跳出“孤立”决断的状态,有互相商量达成一致的机制,他们才可能做出真正“双赢”的选择,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实质上,罗尔斯所说的“孤立”问题源自于“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一个经常被人们讨论的例子是:村民们共有一片山坡上的森林,为了每个人的利益,人们争先恐后地将树木砍伐卖钱。然而,这种孤立选择的最终结果却是:树木被过度砍伐、引发山体滑坡,给村民们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家园不保。“个人理性”追求个人利益,而“公共理性”追求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比比皆是;在霍布斯的契约理论中,强制权力的作用就在于将“个人理性”转化成“公共理性”,将孤立的“个人”整合成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正像《利维坦》著名的扉页图片所展示的那样,无数的小人组成一个巨大的人。所谓国家,就是“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 ;而作为国家之基础的政治制度则是通过某种设计,为人们的自利行为设定规则,并以强制权力保证这一规则的有效性,使人们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增进公共利益。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制度就是无效的、坏的制度。
在罗尔斯对霍布斯契约理论的解读中,某种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确信”:“(确信)的目的是要使合作双方确信共同的协议会被执行。任何人贡献的愿望都是依他人的贡献而定。”举例来说,所有渔民都知道如果一直打鱼而没有休渔期的话,打到的鱼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由此,渔民们约定一年中的某几个月为休渔期,然而这一协议能够得到实际执行并发挥效力的前提在于每个人都按照协议内容去做,而每个人都按照协议内容去做的前提则是每个人都“确信”其他人也都会按照协议去做。否则的话,自己按照协议去做就是“不理性”的。不按照人们共同的协议去做的人,通常被称为“搭便车者”(free rider)。这样的人就像要坐公交车却不愿交车费的“逃票者”一样。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别人越是按照共同协议去做,他就越容易获利。如在“休渔期”的例子中,越多的人按照协议在某几个月中不打渔,那么个别违反协议的“偷渔者”就能偷到越多的鱼。所以,罗尔斯认为,“为了维持这样一个体系——从每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体系是优越的,或者无论如何比缺少体系要好——中的公共依赖,某些罚款和刑罚的手段必须被确立。正是在此,一个有效率的专权者的存在,甚或对其效率的一般信赖本身,都具有一种关键的作用。”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确实强调了强制权力对于形成政治共同体以及保持政治共同体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在阐述国家的形成时,霍布斯论述到:“根据国家中每一个人授权,他(主权者)就能运用托付给他的权力和力量,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抵御外敌。”霍布斯也进一步阐述了强制权力在“建立确信”以及保证人们的共同协议的有效实行中的作用:“信约本身只是空洞的言辞,除开从公众的武力中得到的力量外就没有任何力量来约束、遏制、强制或保护任何人;所谓从公众的武力中得到的力量,指的是从具有主权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不受束缚的集体的手中取得的力量。”由此看来,罗尔斯对霍布斯关于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解读是准确的。
根据罗尔斯对霍布斯的解读,在人们走出自然状态、结成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要消除“孤立”的个人选择,并建立对他人遵守规则的“确信”。在霍布斯的理论中,这两者都离不开一种合法的强制权力的存在。换句话说,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存在都依赖于凌驾于其上的强制权力。无论强制权力的来源为何,这一权力的存在与秩序和制度的存在是同一的。在霍布斯看来,即使是绝对的专治,也比没有强制权力、人们自相残杀的自然状态要好。然而,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对于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且引入了“正义感”这一概念,试图取代强制权力的重要位置,为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寻找更为牢固的根基。
二、“正义感”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专门用一章论述了“正义感”的相关问题。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感”是人们的一种道德情感,它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相辅相成:“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也是一个由它的公开的正义观念来调节的社会。这个事实意味着它的成员们有一种按照正义原则的要求行动的通常有效的愿望。……当制度公正时,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
罗尔斯认为,人们行为公正的愿望并不是对各种专断原则的盲目服从。一种道德原则必须激发人们的情感以及按照原则去行动的欲望,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正义感,正是这种由道德原则所引发的情感。对于道德原则如何进入到人们的情感当中,罗尔斯认为有四个因素促成了道德与情感的结合:第一,道德原则指明了发展人们的共同利益的方式,甚至直接指向幸福,这激发了人们维护正义原则的情感要求;第二,正义感与人类之爱 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由同样的正义观所规定的;第三,持有特定正义观的人们对他人遭受的不公正和伤害感到义愤或有负罪感;第四,根据康德的说法,按照正义原则而行动,是自由平等和有理性的存在物的本性。由此,正义感这种基于某种道德原则的情感在特定的正义观念下,建立起人们之间的友谊和纽带,成为秩序良好的政治共同体的稳固根基。
罗尔斯还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追溯了“正义感”的形成,从道德心理学的三条基本法则中推导出“正义感”:
第一法则:假如家庭教育是正当的,假如父母爱那个孩子,并且明显地表示出他们关心他的善;那么,那个孩子一旦认识到他们对于他的显明的爱,他就会逐渐地爱他们。
第二法则:假如一个人由于获得了与第一法则相符合的依恋关系而实现了他的同情能力,假如一种社会安排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那么,当他人带着显明的意图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并实践他们的职位的理想时,这个人就会发展同社团中的他人的友好情感和信任的联系。
第三法则:假如一个人由于形成了与第一、第二条法则相符合的依恋关系而实现了他的同情能力,假如一个社会制度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那么,当这个人认识到他和他所关心的那些人都是这些社会安排的受惠者时,他就会获得相应的正义感。
罗尔斯的上述推导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亲人的关怀和爱中长大,那他就能习得爱和同情的能力;第二,这种亲人之爱在一种公正的社会安排中则转变为对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友好情感和信任;第三,在确知为公正的社会制度中,对同胞的信任和友好情感转变为正义感。
在解决了正义感如何形成的问题之后,罗尔斯将“正义感”用于解释政治制度的稳定性问题。罗尔斯首先阐述了霍布斯的观点: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在于凌驾于其上的强制权力。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这一论断的依据在于“消除孤立”和“建立确信”——人类合作以及规范这种合作的某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这两个关键步骤——都依赖于某种强制权力的存在。为了反驳霍布斯的观点,罗尔斯论述到:“假如人们具备了这些自然态度和去做公正的事的愿望,就没有人希望以不公正的损害别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利益,这就消除了第一种不稳定性。而且,由于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些倾向和情操是通行的和有效的,任何人就没有理由认为他必须违反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于是第二种稳定性也被取消了。当然,某些违反还可能发生,但是当它们发生时,从友谊和相互信任中产生的负罪感和正义感就会重新恢复公正的安排。”罗尔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自然态度和去做公正的事的愿望”指的是人们的“正义感”,而“第一种不稳定性”对应于前文所述的“孤立”,“第二种不稳定性”对应于“确信”。由此,罗尔斯对霍布斯的反驳可以归纳为:“正义感”可以很好地解决“消除孤立”和“建立确信”的问题,解决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根本困难,为规范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制度构建稳固的根基。
三、“正义感”能否替代强制权力?
罗尔斯的论证是否成功地反驳了霍布斯的观点,“正义感”是否能替代强制权力,成为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必要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正义感的形成是否依赖于强制权力的存在。如果社会中人们正义感的形成仍然依赖于某种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强制权力的话,正义感就无法代替强制权力成为政治制度稳定性的根基。
罗尔斯在阐述道德心理学的三条法则,并在其基础上推导出人们的“正义感”时,颇费心思地讨论了“以德报德”的重要作用。罗尔斯认为,以德报德——“因为我们认识到他们希望我们好,我们也就关心他们的幸福” ——是一种互惠的观念,“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学事实” 。正是基于这一“心理学”事实,罗尔斯才可以从“亲人之爱”推导出“同胞之友谊和信任”,再从“同胞之友谊和信任”推导出普遍的“正义感”。但是,即使假定“以德报德”确实是一个心理学事实,我们仍然面对着另一个难题:如何确定他人对“我”的“德”。
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一下罗尔斯推导出“正义感”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在形成“亲人之爱”的推导中,确定他人对“我”的“德”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要确定双亲对孩子的爱,这是一个基于切身经验就可以判断的事情。父母对子女嘘寒问暖、为了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勤奋工作、为子女争取优质教育资源而做出各种努力……无论是日常小事还是家庭重大决定都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父母对子女的爱。可以说,对于“亲人之爱”的确定是直观而切身的,也是很难质疑的。
然而,推导的第二步,“同胞之友谊和信任”的形成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罗尔斯认为形成“同胞之友谊”的限定条件是:第一,“一种社会安排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 ;第二,“他人带着明显的意图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并实践他们的职位的理想” 。我们可以参照“休渔期”协议的例子来分析这个问题。假设渔民们通过商议确定了一种大家都认为是公正的休渔期方案,并且都表示愿意按照协议去执行。这时,一些个别渔民还有可能“偷鱼”,那么其他的渔民如何才能确定所有的渔民都会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呢?也就是说,罗尔斯在这里给出的“同胞之友谊和信任”得以成立的两个条件中,即使假设第一个条件成立——“一种社会安排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第二个条件如何才能成立呢?实际上第二个条件涉及的恰恰是罗尔斯在批驳霍布斯时所讨论的“建立确信”的问题:人们如何确信人人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罗尔斯回答说,正义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正义感形成的关键步骤中,也需要“建立确信”;那么,这种确信从哪里来呢?在这里,罗尔斯实际上陷入了循环论证:正义感可以消除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性,因为,正义感可以在人们之间“建立确信”;而正义感的形成也需要“建立确信”,那么在“正义感”形成之前,如何在人们之间“建立确信”呢?罗尔斯的推理显然将我们带进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死胡同。
罗尔斯循环论证的问题在其第三步推导中也有体现。罗尔斯认为,在下述两个条件下能形成正义感:第一,“社会制度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 ,第二,“一个人认识到他和他所关心的那些人都是这些社会安排的受惠者” 。这里论证的漏洞仍然是:即使人们认为社会制度是公正的,人们怎么才能知道,社会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施行,每个人都切实按照制度的要求去做了呢?现代社会是一个脱离了村社、部落、家族的社会,现代人日益原子化,成为政治共同体中孤单的个体。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通常通过媒体的传播——广播、电视、网络、自媒体——才能知道那些他们所关心的人是否是社会安排的受惠者。然而,假如媒体报道的内容大多是各种丑闻和不公正的事件,让公众大为惊恐,在这样的情况下,正义感如何能够建立呢?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在罗尔斯给出的“正义感”的形成步骤中,建立公众对于他人行为正义的“确信”是一个关键。然而,罗尔斯并没有给出在强制权力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如何才能“确信”他人行为正义。如果霍布斯是正确的:强制权力能够解决“确信”的问题,那么正义感的形成依然依赖于某种强制权力的存在。也就是说,正义感无法替代强制权力成为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根基,因为正义感本身也依赖于强制权力。
站在霍布斯的立场,我们可以这样来反驳罗尔斯:在与一整套赏罚制度相对应的强制权力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将更容易确定“他人会带着明显的意图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并实践他们的职位的理想”(这是形成“同胞之友谊”的必要条件)。因为人们相信,如果他人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受到惩罚。人们也更容易确定,“他和他所关心的那些人都是这些社会安排的受惠者”(形成“正义感”的必要条件)。因为人们相信,执法者会对不公正的安排进行调整。由此看来,罗尔斯的论证暗含循环之弊端,而霍布斯的主张则更有说服力。
四、小结
综上所述,在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问题上,罗尔斯认为,正义感可以在政治共同体的两个关键问题——“消除孤立”和“建立确信”——上替代强制权力。然而,在罗尔斯对正义感之形成的论证中存在着循环,没有意识到正义感的形成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着强制权力的存在。这使得罗尔斯的观点——正义感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变得非常可疑。
罗尔斯与霍布斯之争涉及何为政治制度之根本的问题。罗尔斯认为,在政治制度是正义的前提下,社会成员之间会形成一种共同维护这一政治制度的道德情感,而这种道德情感是政治制度得以稳定和延续的关键。霍布斯却认为,政治制度之稳定的根本在于与一套赏罚制度相对应的强制权力的存在。可以说,罗尔斯提出的是维护正义的社会秩序之“德治”的建议;而霍布斯强调的则是维护秩序之“法治”的主张。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政治思想向来强调“法治”。然而,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告诉人们,单纯的“法治”是无法成功地维护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至少,执法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操守才有可能使法律得到恰当的施行。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执法者必须具有“正义感”,才有可能通过法律的施行而维护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得到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授权的强制权力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这一权力是任何稳定的政治秩序都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主权与政治共同体是同一的。没有主权,就没有政治共同体,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然而,正因为霍布斯所强调的国家强制权力需要得到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授权,所以该政治共同体之稳定秩序的形成和延续就不能不依靠所有成员的支持与认同。如果共同体成员认为某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是正义的,而其中的成员都能得到相对公平的对待,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将得到越来越多共同体成员的自觉维护,也将更加稳定。由此看来,“法治”与“德治”两者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都具有根本重要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文章来源:
《哲学动态》2018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