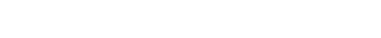作者简介
高放,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家、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高放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等领域问题的研究,以勤勉的治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学术观点,丰富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理论界享有很高声誉,被学术界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一、1956—1957年
我国第一次提出要独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弗·恩格斯于1874年7月1日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留下千古名言:“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可是在我国,直到事隔80多年之后,即1956-1957年才开始在学术界提出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和学科来研究。例如,我写于1956年底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发表于1957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教学与研究》第4期。
为什么我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研究起步这么晚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其一是,自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传播以来,我国首先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学术界人士长期主要致力于研究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当时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并非当务之急。其二是,长期受苏联理论界影响。自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来研究,并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共强调以列宁主义为指导,但是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是以斯大林的个人论断为准绳。1938年出版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由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更是以斯大林总结的苏共党的历史经验作为马列主义的最高成就,在高等院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向学生广为灌输。1950年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时照搬苏联经验,我就是从这时起执教这门课。1949年11月创办中国科学院,也按照苏联经验,设有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却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
直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了斯大林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错误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错误后,才促使我们考虑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改革问题。原来我们按照苏联经验,开设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课,另加一门“中国革命史”。1956年秋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带头,把讲苏共党史的“马列主义基础”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先在三年制的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生班试行,我当时担任班主任,自己边学边教国际共运史,其内容比原先的苏共党史更为广泛丰富了。当时我又感到:本科学生,尤其是理工科本科生要学国际共运史,负担过于沉 重,所以我主张把“马列主义基础”改为“科学社会主义”;考虑到中学阶段已学过中国革命史,所以我又主张大学阶段只按照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把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都上升到理论高度,融入科社这一门课。为了把我独立思考的意见公诸于众,我于1956年10月12日写成《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兼试谈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的改革问题》,送交我校主办的指导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文中绪论部分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学习科社的目的和方法,提出了科社的研究对象是无产 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律,勾勒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包括十个问题,即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问题、民族殖民地问 题、战略与策略、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对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本文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与当时由教育部组织的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大纲不一致,他们提出的教学大纲只讲五个问题,即依据党中央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总结的苏联革命和建设五条基本经验,那就是共产党的建设和领导,经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消灭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认为党中央文件所总结的这五条经验并不是为我们所编科社教学大纲用的,科社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和课程,要学习、讲授一学年,教学大纲理应比这五条划分得更细、更多一些,所以我才提出了包括以上十个问题的体系。到1957年2月14日我又对拙文作了修订。《教学与研究》总编辑认为教学大纲究竟划分几个问题为好可以展开争鸣,所以在1957年4月第4期还是发表了拙文。可是5月底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本来我还站在反右派斗争的前列,在全校大会上和报刊上发表批判右派的言论和文稿,可是到反右派斗争转入本单位后,竟把我的上述关于科社体系要包括十个问题的文章上纲上线为“反党大毒草”,另加上我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发表过《列宁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计划》以及平时在学习讨论会上我就当时国际问题发表过的一些被认为是错误的看法(如说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试验有可取之处),七拼八凑一起,认定我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刻意要把我划为右派分子。幸好吴玉章校长看到批判我的材料后明示:“高放同志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样才使我幸免于难。由于反右派斗争后全国高校都停开所有政治理论课,改学“社会主义教育课”,教育部组织几个院校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大纲也流产了。总之,1956-1957 年,我国报刊上发表过包括拙文在内三五篇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才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在我国学术舞台上第一次亮相闪现,然而犹如昙花一现,迅即枯萎了!上述我在1957年4月发表的那篇文章可以说是科社这门科学和学科在我国第一次闪现中留下的一个鲜明足迹,拙文后来一字不改收入1994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本文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第239-251页)。拙文首次提出科社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律(这在当时是依据毛主席1955年3月31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结论部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逻辑起点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基本范畴可以说就是我所开列的十个专题的标题,这十个专题就是我最初设想的科社体系。拙文当今看来还较粗糙、肤浅,但是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的历史上却具有开创性。
1958年7月我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提升为马列主义基础系,分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政治学两个教研室。1960年9月我系名称改为马列主义政治学系,1964年5月又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增设帝国主义政治和民族解放运动两个教研室。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政治学教研室编写出包括十个专题的马列主义政治学纲要,并且开设、讲授马列主义政治学这门课程,科学社会主义并未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和学科来研究。全国各大学情况大体也都是如此。
二、改革开放以来
我依然持续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从1966年至1976年,饱受“文革”十年浩劫之害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1977年全国深入批判江青等“四人帮”推行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谬论中,迫切需要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当年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胡耀邦及时提出要在中央和地方党校、军事院校以及部分高等院校都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这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得以独立研究并且形成一门独立科学和学科的新举措和新起点。胡耀邦是我们党领导人中倡导并且决定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中央党校可以说是科社这门科学兴起的基地。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在停办八年之后恢复,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成仿吾被任命为新校长。他遵照胡耀邦要加强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工作的意见,把我们国际政治系改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系(1984年后又改名国际政治系),增设科社专业招收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政治学教研室也改为科社教研室。山东大学和华中师院等院校也设科社系或科社专业。1980年7月教育部在《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试行办法》中规定在高等学校文科开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课。全国各级党校都设科社教研部或教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社科院大都设有科社研究部门。从80年代起,设立科社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院校逐步增多。1983年成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有关科社的期刊和论著越来越多。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科社这门科学和学科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逐步茁壮成长。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我早在1956-1957年发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来研究”的呼声终于得到实现了。
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科学从1977年在我国开始建立,迄今才有35年的历史(哲学已有2000多年历史,经济学已有500年历史),科社在世界范围才有100多年历史,许多问题还有待我们持续深入研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长期执教国际共运史这门课程,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全国国际共运史专业第一个博士生导师,随后主编过三本国际共运史教材,担任过《国际共运》杂志主编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和顾问,出版过近75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文集。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依然持续执着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对科社学科建设和专题研究发表过很多个人管见, 以致校外很多人都以为我在人大校内是长期教科社这门课的。我为什么首先选定、特别重视研究科社呢?这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广泛兴趣,而是因为我坚信科学社会主义是长久指导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一门首要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科社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创造。我认为国际共运史的教研也要以科学社会主义(又称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在科社方面出版过一本专著,即《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发表过100多篇文稿,约100多万字,大部分已收入我的两本文集,即《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后一本最近被评为优秀理论著作,已作为“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近日再出增订版。可以说我在科社方面的研究成果远超过我从事的国际共运史专业。
我持续研究科社,提出较多个人的新见解,以下只能扼要概述学科基础建设方面的三个问题。
首先,我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性、首要性及其与社会主义科学的关系。
我不同意一些同志断言科社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说它只是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引申出来的结论;也不同意另一些同志断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或政治经济学。我认为科社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石的一门独立科学,而且它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核心,它是比哲学更直接、比政治经济学更全面指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门首要科学。既然是首要科学,理应成为我们同行同仁以及广大有志建设理想社会、理想世界青年首选的一门科学。当然,也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科社这一个部分,也不能把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为仅是为科社奠定理论基础。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是各自独立的一门科学。科社工作者理应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以及其它组成部分全面了解,融会贯通。我还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虽然有紧密联系,但是还有区别。社会主义科学是首要的一门大科学或大学科,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科学的基础理论科学,一如政治学是政治科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是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社会主义科学还包括社会主义历史学、社会主义现状学、社会主义未来学、比较社会主义等等。我国近几年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列为一级学科,这样就难以再把社会主义科学再列为一级学科。我建议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中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科学的研究。山东大学已经把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改名为社会主义科学专业,扩展了研究范围和内容。
其次,我主张把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学科的名称改名为社会主义学。这样有四个好处:第一,与其它科学和学科的名称一致,如哲学、经济学等等“学”字都放在后头;第二,表明科社是逐步完善的一门科学,并非从它诞生起就十分完满;第三, 其内容也更加宽广,除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体之外,还能对其它多种社会主义思潮和理论作出评析;第四,便于使科社与法学、政治学分开,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如前所述,我本来是在国际共运史教研室,1983年学校把我调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1988年学校又决定把当代社会主义教研室合并到科社教研室。这时我建议把科社教研室改名为社会主义学教研室,课程名称也改为社会主义学。可是未得学校领导同意。他们认为哲学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至今都未改为哲学教研室,所以科社教研室与课程名称也不能改。从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恢复出版报刊复印资料起,就聘请我担任“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门类的顾问。我曾经向书报资料中心领导人建议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门类改名为“社会主义学”。他们觉得这个名称太新,但是还是采纳我的部分意见,从1994年起把“科学社会主义”改名为“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田仲文同志联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陆善功同志找我,要我牵头主编一本供电大使用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我主张改名为《社会主义学》,他们认为言之有理,欣然同意。我们组织8个人合作,最终于1990年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命名为《社会主义学》的教材。随后由于电大不开设这门课,所以此书没有再版重印。这本《社会主义学》,我是以社会主义学纵向发展的五种理论形态为主线来划分章节,这五种理论形态即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当前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和未来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12月天津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约请我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述略》一书,作为该出版社策划的“学术研究指南丛书”之一。我在此书书名之下特意加上“社会主义学导引”副标题。我在前言中着意说明加上这个副标题“这是有特别用意的。”也就是要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学科改为“社会主义学”。从1990年起,我还组织南京师大和南京陆军步兵学院等校教师另主编一本《社会主义学》,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归纳出的十八个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构成体系,本想以此书与上书构成《社会主义学》的姐妹篇。这十八个基本问题的体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的出路,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生 产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前景。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和1991年苏联剧变后,国内“左”的思潮上升,各章执笔者大多不敢按照我的见解来撰写,我在统修中又不便对初稿的观点作重大改变。例如第一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出路,我认为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已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初稿作者依旧认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果我把它改为社会资本主义,这 已不是他的观点。由于未能按照我的见解统稿,本书终于未能出版,实在遗憾!好在1988年初国家教委决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全国高校硕士生的一门公共理论课,政教司要我们科社教研室提出教学要点。另一位同志提出按科社十几个基本原理编写教学要点,领导上认为过于陈旧,缺少新意。由我设计的一个纵横交错、理论联系实际的包括五个专题的教学要点,得到国家教委政教司认可。这五个专题是:第一,科社理论的形成和初步实践;第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具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第四,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世界各类社会主义政党的新变化与新探索;第五,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命运。按照这个教学要点,由我带头,有六位教师分工先在校内外讲授, 然后合编一本《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第一版。我在本书绪论中论证了把科学社会主义改名社会主义学的四个理由、四个好处。很多读者都表示赞同这个看法。我主编的这本书由于体系新、内容新、观点新、材料新,广受社会欢迎。但却受到思想保守者封杀,结果反而更加畅销。第一版只印5千册,1994年第二版增为20多万册。从2003年第三版起我联合李景治、蒲国良共同主编,2005年出第四版,2008年出第五版,累计印数又新增30多万册。出版社已约定我们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还要再出第六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也采纳“社会主义学”这个名称。我手边还保存一份2004年该研究所的《社会主义学》课程授课表,内分十五个讲题。其中“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主义学”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两个讲题,就是约请我主讲的。当今还有人提出:如果建立社会主义学,那么是否还要建立资本主义学?其实资本主义学早已建立。我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论著早在18世纪就奠定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论著则是19世纪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学的经典文献,美国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是当代资本主义学名著。
最后,对科社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它的研究对象问题,我也不懈努力进行探索。关于科社这门 科学的研究对象,我先后三次提出管见。如上所述,早在1957年我在《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一文中认为:科社是研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律。这显然是受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1978年5月下旬我应邀在杭州大学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上再次呼吁“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划分开来,并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划分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开设。”这时我对科社研究对象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1957年的看法上。1982年我在《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开始改变看法。书中提出:科社“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到1985年9月9日我在《光明日报》“科学社会主义”专刊第72期发表《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新看法》(此文漏收入我的文集)。文中检讨了我以前两种旧看法的不妥之处。1957年我主张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律,只从无产阶级着眼,过于狭窄,有很大片面性,现在看来是不妥的;1982年我只谈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没有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包括在内,因而也是片面的,有缺点的。我也不同意当时大部分科社教材还以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或者再加上“一般进程”作为科社研究对象。我在此文中提出的新看法是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改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在1990年7月和1994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由我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关于科社的研究对象,我还是沿用了上述新看法。2003年至2008年出版第三、四、五版,我又把科社的研究对象简化为研究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涉及科技、经济、政治、法治、文化、教育、生态、民生、国际关系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所以依照我个人体会,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指导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门首要科学和广大青年首选的一门科学,而且还是一门首广科学,即是说它的研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当然它不是分门别类去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问题,而是综合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在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中综合运作和变化的一般规律。可以说科社是一门以政治为先导的综合性理论科学。由于科社是一门首广的科学,所以它又是一门首难 的科学。研究者必须具有深厚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必须深切了解国内外社会的现实情况。依照我个人亲身经历的体会,科社不仅是一门首要科学,首选科学,首难科学,而且还是一门首险科学。党要求我们勇于创新,要求创先争优,但是在科社这个学科尤为艰难。因为按照传统惯例, 对科学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论断都是必须以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为依据,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是以列宁、斯大林的言论为依据。随后又以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言论为依据。由于长期盛行个人崇拜,加上屡有源远流长“右”的干扰,更常有根深蒂固“左”的危害,学者主要只能限于注释、讲解领袖的言论和党的文件,个人是很难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回想1956年我因同意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言论, 发表了一篇《列宁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又不同意按照党中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总结的五条经验来构建科社教学大纲的体系,结果险些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被连续批判二十年之久。到80-90年代,我又因对科社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科社的研究对象、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还被思想保守者乱扣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有人指责我不该把科社对象表述为“改变资本主义世界”,而必须说“推翻资本主义世界”。殊不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是这样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制,有人认为其实质是集中制。我认为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有人认为是一党制。这些本来都是可以探讨、商榷和争鸣的理论问题,可是由于“左”的积习很深,所以迄今依然难以深入研究。
现在有很多年轻同志加入科社教研队伍,这表明这门首要科学、首选科学后继有人,令人振奋。既然投身这门首要学科、首选学科我们就要义无反顾、责无旁贷把这门首要科学持续研究到底。由于科社又是首广科学、首难科学、首险科学,我们就要善于广中选点,避难就易,脱险居安。也就是说要在尽量广泛充实自己的同时,选择几个重点问题,避开那些难度很大、风险很大的问题,作为自己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这样锲而不舍,日积月累,就必能多出优秀成果。我由于长期教苏共党史,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曾经情有独钟,苏联剧变令我揪心剧痛,进而认真总结其失败原因和教训。去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纪念,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文集,收入我六十年来针对苏联兴亡发表过的66篇文稿,约55万字。简而言之,我认为苏联能够兴起、兴盛正是由于遵循并且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苏联终于衰落、败亡在于教条式照搬甚至背离科学社会主义。上海《探索与争鸣》杂志今年第七期已发表了周尚文、叶书宗两位教授对拙著的评论。中联部当代世界中心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同志也写了一篇书评, 即将在《当代世界》发表。前两天他打电话对我说:他读后感到这本书是“三最”(起步最早、涉猎最广、见解最深)、“三真”(含真情、说真话、护真理)、“三不”(不唯书、不唯上、不随波逐流)。
我十分赞赏清朝名儒戴震的名言:“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在封建主义时代,有良知的学者只能“独寻真知”,只能“启后人”。在当今社会主义时代,我想应该把他后一句话改为“众寻真知启世人”。我们科社教研工作者理应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大力繁荣科社这门首要科学,为资政育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