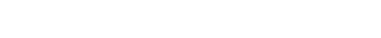编者注
本期简报摘编自《国际论坛》2024年第5期,第12-18页。
2024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正副总统、全部国会众议员、约三分之一国会参议员、多位州长以及其他地方官员都将面临改选。此次大选新产生的美国联邦政府等各层次机构将塑造美国的内政外交走向,其中总统因其在对外事务上的关键主导角色而备受关注。特别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代表共和党参选、存在回归可能性的情况下,本次选举给美国以及世界带来的影响更值得密切观察与深入探究。可以说,这场关于特朗普是否会重返白宫的选举,不亚于一次两个不同方向的美国之间的对决。在过去近八年中,特朗普政府正式开启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则加以延续与调整。基于这一事实,两党对决是否会涉及对华事务、未来四年由谁来主政白宫并继续推进美国对华战略,毫无疑问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牵动乃至影响。
一、选举过程与中美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选举从初选到大选一般都要经历10个月左右的选举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一是中国议题是否会被较多炒作甚至成为主要竞选议题,这将直接影响两党候选人的对华政策阐述以及未来上台后的对华政策走向;二是在任总统是否会从自身或本党选举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利用行政权力插手对华事务,这将对中美关系带来直接影响;三是非总统党一方如何阐述对华事务,这将为其如果当选后的对华议程提供评估参考。
就选举议题而言,在2024年大选过程中,中国议题显然并非首要关键议题。根据相关民调与研究,经济与通胀、移民与边境管控、福利与医疗、生命权与选择权以及国际冲突等议题在本次选举中吸引了美国选民不同程度的关切。其中,国际冲突议题主要聚焦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这两场冲突虽说都涉及大国关系,但与中国议题并不存在直接联系。在不同层次选举中,某些两党政治人物仍提及甚至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但这些炒作基本源自明确的国内议题,属于当前美国国内关键议题的外化与延续,并非关键国际事务。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两党在中国议题特别是对华战略定位与方向上的相对一致性。
就在任者政策而言,拜登政府在对华事务上表现出保持正面对话的同时又负面操作某些议题的两面性。一方面,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被拜登政府视为关键“业绩”。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持续延宕、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拜登及其民主党阵营在对外政策上可以标榜的所谓“业绩”乏善可陈,甚至这些国际冲突的发展态势对其自身以及民主党选情也带来拖累效果。基于此,能够稳定中美关系、在持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保持与中方的高层对话与各领域沟通,成为了民主党执政“业绩”的加分项。正如拜登在2024年3月发表《国情咨文》时所言,“我们(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地位来赢得21世纪与中国的竞争”显而易见,拜登及其团队以此刻意向美国国内展现出能够“把握”中美关系、正在所谓“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的架势。另一方面,操作涉华议题也成为民主党阵营提振选情的关键“抓手”。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以及威斯康星等中西部三州再次被视为总统大选的必争之地,为了增加胜算,2024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在与三州利益相关的海事、物流以及造船业等产业领域展开对华的“301调查”,并在5月宣布在与三州利益有关的钢铁、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产业领域对华加征高额关税。如此以对华事务作为选举政治“提款机”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损害中美两国各自利益,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随着选举临近,如果民主党阵营选情持续堪忧,不能排除其主导政府再次铤而走险操作涉华议题的可能。此外,在退出竞选但仍为在任总统的情况下,拜登在剩余任期内特别是在选后或将转为所谓“遗产导向”,进而其在对华政策上是否会或如何调整,也存在着一定想象空间。
就非在任者言论而言,特朗普及其保守派阵营在对华事务上有不同程度上较为负面乃至极端的论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特朗普自己录制的所谓“47议程”(Agenda 47)、传统基金会编制的“2025计划”(Project 2025)、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5月初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的“美国优先”范式》(An American First Approach to U.S. National Security)以及多位特朗普政府前高官及被认为与特朗普团队关系密切人士撰写的书籍和政论文章都在不断对外传达着内外政策的各种可能性,涉及对华事务较多。在初选阶段,特朗普本人就曾抛出将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至少60%关税的言论。特朗普政府的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则直接提出,要通过终止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加征关税、放弃世贸组织等做法来终结“中国数年来损害美国利益的所谓‘经济战’”。曾任特朗普时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O'Brien)以及副助理马修·波廷杰(Matthew Rottinger)等人也分别撰文鼓吹对华全领域对抗、妄图谋求所谓“速胜”的“新冷战”。担任过切尼(Dick Cheney)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叶望辉(Stephen Yates)等人更是列出了包括加速“脱钩”、强化军事威慑、协防台湾地区、与地区盟友培养强大联盟、终止对华高校与研究机构合作、禁止孔子学院(课堂)以及中国学生社团活动、重塑稀土全产业链、禁止中方在美投资置地、封禁TikTok以及其他涉华应用程序等一系列对华强硬的政策建议。这些论调虽然仍为竞选语言而远非实际政策,但也引发了中美两国相关各界的关注与担忧,无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舆论氛围与前景预期。
二、选举结果与中美关系
作为本次选举的结果,新当选总统将在2025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职,其组建的内阁班底以及白宫政策团队也将随之陆续就位,从而形成作出内外决策、推进内外政策的美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核心圈层。这些变化必然涉及到对华事务,进而涉及到中美关系。
在过去将近四年中,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并在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直接将中国定位为“唯一具有意图并具有持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以及科技能力来改变国际秩序的竞争者”,提出要“竞赢”(out-compete)中国。具体而言,拜登政府延续并调整了特朗普政府开启的所谓“印太战略”,持续修复盟友关系并推进所谓议题联盟的“小圈子”,强化高科技领域的对华“脱钩”,制造地区安全紧张,插手台湾问题,对华展现出长期且系统的战略竞争。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重新回到了对华高层与各层次沟通的正面轨道,以此推进对其有利的某些合作,管控对其不利的所谓风险。从本质上看,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战略中正在构筑一个战略“区间”——区间上限是不让中国在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超越美国,区间下限是不与中国发生美国不希望卷入的高烈度冲突。保持上限的手段是美国以自身和联盟的优势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保持下限的手段是通过与中国沟通管控风险升级。如此区间所形成的就是所谓“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其在为中美关系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基本稳定提供可能的同时,事实上也为美国自身内外的调整与重建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换言之,与共和党某些人展现出的所谓“速胜”相比,基于对华战略定位的基本共识,民主党的考虑是回避对抗、调整国内、强化盟友、以竞争消耗对手、提升自我,即“投资、结盟、竞争”的所谓“不战而胜”。
如果接替拜登参选的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获胜,得以继续执政的选举结果至少证明了拜登四年相关政策的所谓有效性,进而上述对华战略与政策将大概率得以延续。具体而言,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至少将在哈里斯政府初期得到延续,过去一段时间中美之间各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沟通也将有机会得以延续乃至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上述的拜登政府在竞争与管控之间的两面性,哈里斯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同步延续这两个面向,还是在大选周期压力消散后开始逐渐转向竞争强于管控?如果同步延续两面性,如此不断生成的内在张力乃至矛盾的微妙状态如何调和?即便能够继续维持一定的稳定性,民主党政府完全从自身需求与关切出发的菜单式对话与合作对中美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如果竞争逐渐强于管控,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是否会存在随时被打破的可能性?
如果共和党人特朗普重返白宫,基于其此前执政四年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极端负面影响,中美关系所要应对的首要问题就不是能否或如何继续保持稳定,而很可能是如何应对更严峻且更棘手的不确定性。
第一,从个人层面看,2025年可能再度执政的特朗普与2017年相比会有怎样的区别与变化?八年之前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后续四年的执政可谓震动世界,同时也让世界对于特朗普的个人风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反建制、商人思维、交易、善变、自我、好胜、极限施压、追求相对获益等都被归纳为其个人特质加以讨论,并作为理解其内外决策的关键切入点。如今,经过了四年总统与将近四年前总统的经历,特朗普在对外决策中的个人特质是否发生了变化?在共和党所谓“特朗普化”持续加深的趋势下,特朗普个人是否也受到了某些本党精英的塑造?对特朗普作为决策者个人风格的判断,将成为预测其在对华事务上决策可能走向的重要起点。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基于其个人偏好和国内基础,特朗普仍极为关注对华经贸议题,其上台后的中美经贸关系最可能率先面对重大挑战。
第二,从团队层面看,特朗普的对华乃至对外决策圈将如何构成、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生态?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随着特朗普锁定共和党提名并展现出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包括其政府前高官在内的多位保守派人士纷纷公开发声,阐述特朗普重返后可能的对华政策走向。不过,这些急于公开表达政策立场的保守派人士到底是否会如他们所明示或暗示的那样最终跻身于可能的特朗普政府,仍很难预料。换言之,这些对华政策表述究竟是特朗普的授意,还只是为了引起特朗普及其团队关注的自荐行为,仍无法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要从这些保守派人士的公开政见来描摹特朗普重返后的对华政策,那么就应该梳理出不同议题上的政策范围或政策情景,明确上限与下限,未必要轻易认定在某个议题上必然会如何。与此同时,即便其中一些人甚至所谓的“超级鹰派”最终进入了可能的特朗普政府,特朗普与这个团队将形成怎样的互动生态也事关重大。事实上,在此前四年执政期间,虽然特朗普极为强调忠诚度,但其决策核心圈基本上是各成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伙人团队”,对外政策走向并非完全体现特朗普的个人意图。此次如果重返执政,特朗普是否会要求团队彻底执行其意图,可谓是一个关键看点:如果特朗普如此为之,在那些特朗普与其团队对华鹰派存在分歧的政策议题上就存在一些值得仔细理清的变数。
第三,从议程与手段层面看,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或多大程度上延续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必须看到,虽然在2020年大选期间猛批特朗普,拜登上台后还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换言之,拜登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特朗普政府所界定的。2025年之后,如果重返白宫,在延续对华战略竞争大方向之下,特朗普政府也完全可能接续拜登政府四年的对华议程。比如,在盟友关系特别是拜登政府开启的“议题联盟”或“小圈子”关系上,特朗普完全有可能放弃某些其认为效果有限的内容,但同时也大概率继续推进其认为有效的部分,同时再做出一些具有特朗普个人色彩的难以预期的、甚至是极端的行动。这种状态看似是“拜登的路线加特朗普的节奏”的颇为怪异的“弗兰肯斯坦式”组合,但从本质上看,此组合恰恰意味着,从2017年发动,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或将经历“特朗普开启方向、拜登调整议程、特朗普再延续再调整”的逐渐调试与稳步演进,其结果就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充分系统化定型,该战略进而势必固化并长期存续。
三、变与不变
必须看到,2024年美国大选在其国内政治维度上具有节点意义,将对美国未来的国家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2024年大选加速着美国的内外变化,进而也加速着百年变局的历史演进。
看到2024年大选所引发美国政治与政策变化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其中更多的不变。对当今美国而言,这场选举显然无法改变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转型期,也无法改变其对外战略的收缩调整期。对美国对华战略而言,这场选举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方向与基本态势。对中国对美态势而言,这场选举更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在对美事务上的一贯积极务实立场以及稳定发展两国关系的负责任态度。对当前中美关系而言,这场选举不会改变中美两国人民希望两国关系稳定的共同积极意愿,也无法改变中美两个大国分享的广泛利益、面对的多重挑战以及担负的全球责任。
过去五十多年,中美的互动与建交改变了世界,展现了中美两国的世界责任与全球贡献。未来五十年,中美能否找到新的正确相处之道、能否继续展现世界责任与全球贡献,对全人类的共同前途与命运而言至关重要。从前后五十年的历史视野出发,2024年大选只是一个节点,或许会引发风浪,但改变不了中美大国关系历史潮流的大势。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