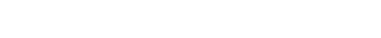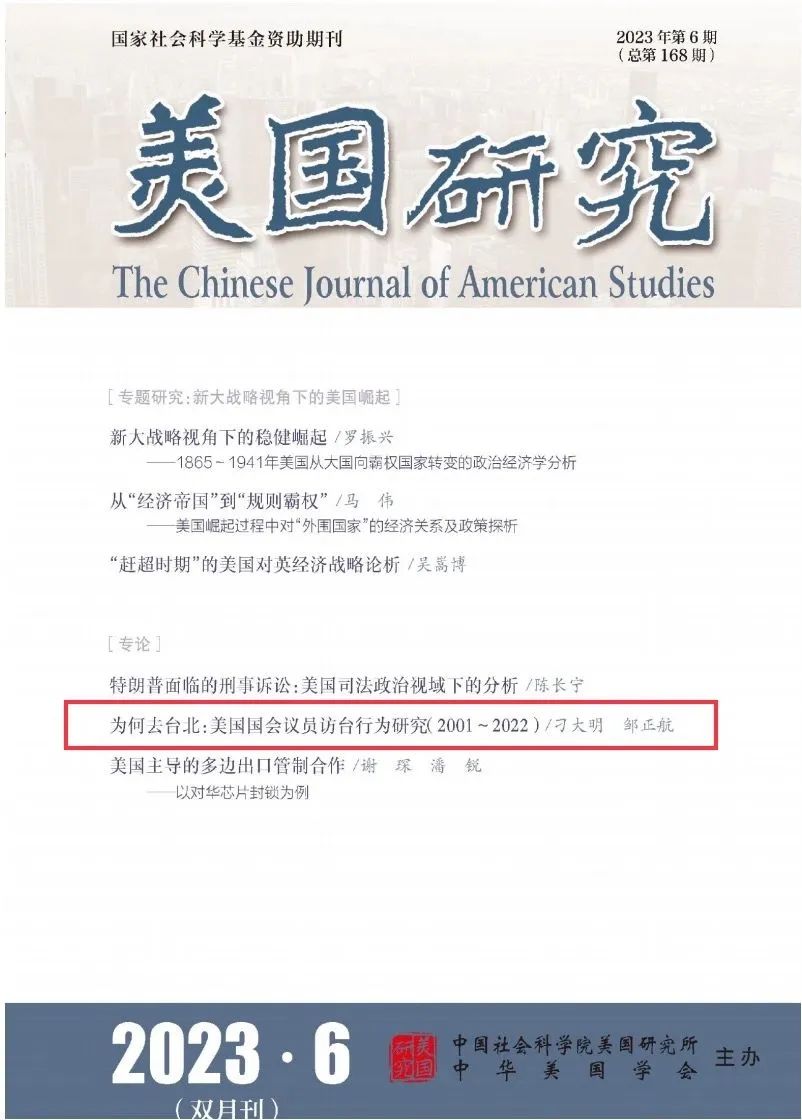本期简报摘编自《美国研究》2023年第6期,第100-125页。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趋势与逻辑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邹正航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系硕士研究生
2022年8月2日至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时任议长南希·佩洛西悍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导致了台海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频繁访台的历史。基于美国国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相关部门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与数据,新世纪以来即第107届国会(2001-2002)到第117届国会(2021-2022)期间,已有177个国会议员代表团的253位、363人次的国会两院议员到访台湾地区。就访台议员的两院分布看,在第107届到117届国会期间,众议员访台多达292人次,参议员仅为71人次;就访台议员的党派归属看,在第107届到117届国会期间,共和党议员的访台人次(203人次)超过了民主党议员(160人次)。
一、美国国会议员外访行为的一般逻辑
美国国会议员外访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目的地,已成为议员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施展个人外交能力的直接且重要的手段。
第一,国会议员通过外访对外交事务加以调查研究,为对外政策相关立法提供判断依据。
第二,国会议员在外访期间直接与相关外方接触沟通,推动符合其代表利益的政经军事合作。
第三,国会议员在外访期间更易与同行其他议员建立个人联系和关系网络,有助于化解分歧、形成共识。
第四,国会议员以外访敏感地区来申明自身立场,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资源。
二、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总体趋势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总体发展趋势存在着明显的多重驱动线索。
第一,美国各届政府的对华战略特别是“对台政策”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国会议员的访台行为。当需要稳定中美关系时,美国往往恪守承诺,不希望台湾地区成为“麻烦制造者”,特别是面对岛内所谓“台独”势力的相关动作时更多予以施压抑制,总体上限制国会议员访台的空间。当要推动对华战略遏制时,美国则主动炒作介入台湾问题,“以台制华”。在“放任”“默许”乃至“邀请”之下,国会议员更易通过访台等行为与岛内某些力量联动,肆无忌惮地共同制造事端。
第二,不同府会关系及其形成的党争态势影响着国会议员的访问行为。通常情况下,由于不满非本党总统的对华战略及政策,国会议员凭借访台等行为来公开宣誓立场、平衡乃至介入、打乱总统议程,通过“对华示强”来与白宫竞争“对华政策方向盘”。“分立政府”期间非总统党议员比“一致政府”期间出现更为活跃的访台行为。共和党议员在“分立政府”期间的访台行为更为突出,反映出共和党人更易在极端保守意识形态驱动下与民主党总统形成激烈对峙的现实。
第三,岛内“政党轮替”及其导致的对美政策调整影响着美国国会议员的访台行为,但并非最关键因素。2001年以来岛内的两次“政党轮替”都刺激了美方关于所谓“美台”互动的需求、激化了当时美国国会议员的访台行为。按照一般理解,岛内某些势力会通过游说、军购等利益输送来强化与某些“亲台”议员的联系、促使后者做出提出提案、参与连线以及访问台湾地区。但必须注意的是,岛内不同主导政党的情形未必导致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明显差异,甚至在具有所谓“台独”倾向的民进党期间国会议员访台反而总体上略少。这也说明,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仍要配合美国总体政策,而非岛内某些势力通过利益输送就可彻底左右。
三、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个体逻辑
美国国会参与访台行为的议员在个体层面上表现出某些特定特征与特有逻辑。根据对第117届国会期间(2021-2022)国会众议员访台行为进行个案的量化研究,可得出如下发现。
第一,政党、意识形态、性别以及族裔等因素不会对国会议员的访台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近期,国会议员的访台行为已成为两党共同推进“以台制华”的关键表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两党政治人物在对华战略上的负面共识。
第二,新当选者近年来更易参与访台,即新当选或资浅议员往往会通过极端行为来吸引眼球、调动资源。特别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之下,以访台等方式来到大国竞争所谓“最前沿”的“冒险经历”,更可能成为某些新当选国会议员的“作秀”。必须警惕的是,新当选者突出的访台行为正在为岛内某些势力与新世代美国政治人物建立更多联系并施加影响创造机会。
第三,军事、退伍军人事务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更易访台,完全符合以往判断。军事委员会与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背后一般是军工产业利益驱动;军事相关委员会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更多的访台行为展现出在地区战略与对华战略意义上对台湾地区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拜登政府已开始更多重视台湾地区在科技方面的重要地位,但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成员并非更易访台。这或说明目前对台湾地区重视的议题转向、强调科技议题,仍是以军事安全、对外战略角度出发的。
第四,国会领袖至少在第117届国会并非更不易访台,而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在第117届国会期间也并非更易访台。前者回应了佩洛西“窜访”的事实,揭示出某些国会领袖已放弃以往较少参与负面极端涉华行为的一般态势、转而“积极”参与其中,但该变化尚未形成趋势。后者从不同视角印证了一个判断,即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未必是岛内某些势力单方面游说的必然结果,而更多是与美国对华战略方向一致的表现。
第五,来自南方选区或者白人比重较大选区的国会议员并未更易访台。换言之,持有保守立场者未必更易访台。相比而言,来自亚裔人口比重较大选区的国会议员则更可能访台。其初步解释是,选区的亚裔比重较多,则其国会议员往往更为关注亚太、甚至更为关注美国所谓“印太战略”,从而更易访台。
第六,选区对华出口额不产生影响。不同选区的对华出口情况相对稳定,议员的访台行为未必会对其选区对华经贸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相比而言,选区对华出口额呈现出增长的时候,其国会议员更可能不会访台。选区在对华经贸合作中的利益增加,更可能转化为对其国会议员涉华行为的有效压力,从而抑制相关行为。对华出口额增长率越高,却不意味着国会议员越不易访台,增长率越低也并不意味着国会议员就更易访台。该情况极可能意味着,访台行为还是被国会议员认识到是非常极端的对华挑衅行为,进而从维护选区在对华经贸合作中获益的角度出发而选择不访台,而不是增长幅度多少或者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抑制议员的访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