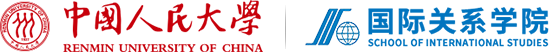来源:人大国关
作者简介
时殷弘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一段时候甚而若干年以来,在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内,某些以开明或自由(liberal) 视野和信念为特征的著名学者和政治人士一直热烈和雄辩地论说一类重大需求,无论是从全人类、跨国共同体和国际社会角度还是从民族国家本身及其国内公民角度来说都至关重要的一类需求,那就是必须弘扬和推进全球治理,同时为此维护、增强或拯救全球开明或自由秩序——全球治理得以弘扬和推进的一大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和“组织构架”。他们的论辩看来大多不同程度地从“应然”优先于 “实然”、必需优先于可能、普遍价值优先于特殊情势的思想方式出发,或者说主要是规定性的,其中富含真知灼见和道义命令,即使对怎样的秩序才是真正开明的秩序可以有、事实上也已经有颇为不同的主张和论辩。
完全能够从大致相反的思想方式出发去考察和论辩,那就是“实然”优先于“应然”,可能优先于必需,特殊情势优先于普遍价值。由此出发,在总的来说认可甚而积极追索上述重大需求的前提下,于辨识供给。倘若本着这供给侧视野,那么在当今见到的图景就颇为不定,甚至颇为暗淡,或者说是冷战结束以来最暗淡的,并且在一般可预见的时期内还很可能看不到隧道尾端的光明。然而,这种看似(实际上也是) 悲观主义的考察可以富含审慎特征,且以具体和求实见长,以至大有助于辨识需求大致得不到满足的要害何在,从而可以对争取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满足需求或在最不理想情况下寻找合适和正当的“退路战略”做出贡献。
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全球治理和全球开明秩序面对严重挑战甚而倾覆危险,即使——让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和发展中世界亿万大众着重重申——对怎样的秩序才是真正开明的秩序可以有、事实上也已经有颇为不同的主张和论辩。惊诧甚至惊恐致使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著名专栏作家疾呼:“民粹主义信条用民族主义取代了爱国主义,鼓励人们蔑视传统机构。任何所谓‘专家’都在与精英勾结。每个人都有权构建自己的‘事实’。大企业、银行、全球化(叫它什么都行)都是白人工薪阶层的敌人。沿着这个方向只要再走几步,就会把我们带回到上世纪30年代‘犹太人的阴谋’。”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力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或两者兼有地)挑战甚而倾覆“锚泊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构造”?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所提示的那样,必须将冷战后美国绝大多数行政当局、发达世界跨国资本、主流媒体和精英自由派学者为主干的自由主义精英本身视为自由主义秩序的首要挑战者,甚而倾覆者。是他们,以一种充分辩证因而大为讽刺性的方式危害了他们自己溺爱、从中得益、以致放肆滥用了的自由主义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多年来以其自私、傲慢、褊狭、盲目和殆无节制的挥霍疏离了他们国内的那么多“草根民众”,尤其是“白人草根”,还有世界上那么多其他民族! 2008年秋季爆发的非常广泛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已经以经济金融方式对他们发出了清楚不过的警告,但他们的盲目和其他恶习竟使这警告差不多如同过眼烟云,非得以英国全民公决退欧和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并且获胜这样的政治/社会方式才能震醒业已惨败的他们。
就此,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W.Hawking)以自由主义精英身份做了严肃的反思。他于2016年12月初在英国《卫报》上发表《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一文,其中指出:“近来在美英两国,显而易见的精英遭拒肯定是针对我,就如针对任何精英一样。不管我们可能怎么去想英国选民拒绝欧盟成员资格的抉择和美国公众拥抱唐纳德·特朗普的决定,评论家们的心里都不怀疑这是民众的愤怒呐喊,后者感到被他们的领导抛弃了。每个人看来都同意,这是被忘怀者发声的时刻,发觉其吼声是拒绝每个地方的专家和精英的劝告和指导。”
按照霍金的观点,这些抉择和决定表现出的忧惧和愤懑出自“全球化和加速着的技术变更的经济后果”:工厂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兴起不仅已经损伤传统制造业的就业状况,也颇可能将“这工作机会摧毁机能”延深入中产阶级,只留下“最精细、最有创造性或最具监控管理性的角色”。由此,全球范围内已在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使之成为可能的互联网和种种平台允许很小一群人获取巨额利润,同时只雇用很少人。“这必不可免,这是进步,然而这在社会意义上也是摧毁性的。”不仅如此,世界上金融不平等正在愈益扩大而非缩小:越来越多的人在少数人愈益富有达致千万甚而亿万的同时“可以发觉不仅他们的生活标准,而且他们简单谋生的能力本身正在消失”。更有甚者,强劲的动能还在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全球性蔓延的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这些不平等的严酷性质现在比过去更显著昭彰和众所周知,因为“对任何不管多穷但仍能用上手机的人来说,世界最繁华部分的最富有者的生活都令人异常痛苦地清晰可见”。结果,经过种种人口迁徙过程、社会互动过程和认知过程,“宽容被损害,政治民粹主义被进一步加剧”。一句话,全球既有秩序——在自由国际主义精英那里的全球开明秩序——已经或至少正在失去它的一个极重要条件: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
正是首先在这样的根本生态中,世界面对“特朗普风暴”,虽然由于他本人都始料不及的那么严重的种种国内制约和反弹——很大程度上出自他的放肆、褊狭、排外和非法行动嫌疑,这风暴尚远未能够充分肆虐。已经非常明显和无可置疑的是,特朗普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开始,到赢得白宫总统宝座,直至当今,从未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制显现过真诚的尊敬,从未对以颇大程度上的社会取向多元化和宽容为特征的当代美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做出过真诚的呼应,也未对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贸体制乃至更广泛的国际和跨国合作表示过真诚的赞许。他是全球开明秩序的“克星”,无论一个人如何定义这里的“开明”,也无论他到头来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事实上,在特朗普选胜以前,人们就可以相当强烈地感觉到某种意义上的“变天 (global political climate change)”趋向: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颇为显著甚至急剧地发生朝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方向变更。美国特朗普—桑德斯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潮流的强劲凸显,宪政民主体制在美国许多“白人草根”选民那里遭遇的相当广泛的心理动摇甚或信念瓦解,英国经全民公投产生的令人意外的退欧决定,比冷战后头 20 年远为广泛和频发的经济保护主义,欧洲国家愈益高涨的反穆斯林移民潮舆论和欧洲极右翼运动的更大的势头等,都表现了这一趋向。不仅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咄咄逼人但颇得国内民心的、与西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激烈对抗态势,土耳其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政权民粹主义的伊斯兰化举措和急剧集权趋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法外反毒、对美攻击、连爆粗口和所有这些至今在菲律宾国内草根民众那里得到的喝彩,都显示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倾向。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表明,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大致一直熟悉的世界面临严重危险。什么是这熟悉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世界绝大多数重要国家以其基本政策赞护的愈益增进的全球化,还有这愈益增进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处粗略而言大致比较有益的经济效应甚或社会效应;在这个世界里,很广泛地存在着相信上述这两点的意识形态信念,或者说有着占显著优势的全球开明政治文化;在这个世界里,不仅中国怀抱主要出自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自信,而且各发达国家也怀抱自信,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前相当充分;在这个世界里,大国之间的关系大体而言相对稳定,而且比较互容和协调;在这个世界里,从战略心理和军事态势上说,美国不那么神经质,中国不那么激进,俄罗斯不那么不顾一切(desperate) ,日本不那么“修正主义”。
现在,所有这些都已改变,或者正在显著地改变。换句话说,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熟悉的世界已经大致结束,或者至少正在结束。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特朗普当选后几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首次,强国和新兴国家同时迷恋种种不同类型的沙文主义……拥抱一种悲观主义观点,即对外事务往往是零和游戏,在其中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争。此乃大变,缔造一个更危险的世界。”顺便说,中国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口号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而又审慎求实地适应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气候变化,甚至是气候剧变。这与消极的随大流是两回事。
与发达世界内部尤其是美国内部出现“变天”趋向的同时,挑战甚而倾覆全球治理得以维持和推进的全球开明秩序的力量还有俄罗斯,那是一个由喜爱冒险但颇有战略意识的普京总统掌控的、不时对西方以及东欧和中亚邻邦咄咄逼人的看似不顾一切的国家。不仅如此,同属这类挑战和倾覆力量的,当然还有一个总的来说动荡不已和殊难稳定的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交错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宗教政治断裂带中东、北非、西亚以及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那里亿万人口严重疏离“现代性”和无论何种世界秩序,但依然顽强固守或渴求恢复其传统的自豪和根本信念。
全球治理面对的重大困难比前面所说的一系列要素还更广泛,甚或更深刻:诸多大国利益严厉限制;某些关键性小国顽固不群;所涉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而且新颖。关于前两点,还可以说得更宽、更广:全球性难题和危险之多发和常在,连同全球治理的必需,那么经常地不符合不同国家和大国确立的各种国家优先事项和优先利益。由于种种原因,在当今时期总的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全球治理在一系列功能领域面临程度空前的困难。无论要治理的问题是同舟共济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威胁、谋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或完成多哈贸易谈判,还是海洋争端和海上行为对立、防止核武器扩散、涌向欧洲的穆斯林难民大潮或“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战争,就这些问题而言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难上加难。几乎罕见的重大例外首推 2013 年以来取得重大进展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事业,依凭中国晚近巨大的主动贡献,还有中美两大首要排放国之间的有效协商和协调,虽然它现在面临被特朗普政府“撤离桌面”的危险。
因此,人们所见的相关局势大多属于适逢“艰难时节”的正常情况:恰在这更需要国际广泛合作和多边体制的时候,往往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 体制创建维艰,或已有体制低效。应然往往远异于实然,当今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远甚于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学说在先前“较好时节”所言所料,其时至少世界经济状况良好得多,同时权势格局变动也窄小得多。说到这里,就不能不突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愈益严重,而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先前任何时候相比,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基本关系可谓强烈动荡。至少到前不久为止,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显著加剧,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协作则作为这两大事态的一个结果而大为提升。尽管特朗普与普京从各自的根本利益出发,急欲谋求美俄关系大幅度缓解和改善,但如前所述,美国国内众多政治阻力远大于特朗普和普京先前想象的,而且美俄之间的结构性地缘政治和战略矛盾非同小可,因而美俄关系大幅度改善即使实现也不易经久。简言之,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所需的基本支柱之一即大国合作原本就不坚固,现在更增添了脆弱性。
需要再度强调,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是全球秩序动荡和“裂变”的重要动能和表现,全球治理的困难由此就更可理解。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一方面仍需要努力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但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全球逆动倾向,认识到单独一国不是足够的全球化国际秩序(或至少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 的稳定器和顶梁柱,甚至还要有“无力回天”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当今中国对于全球秩序有着复杂的意向,这种意向既来自全球局势的复杂性,也来自中国利益和信念的复杂性。
概而言之,当今中国在全球和国际体制性秩序(institutional order)中的基本态势首先是合作者,其次是温和和渐进性的改革者,最后就少数不同的重要问题而言是保守者,就另一些则是激进者;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在全球和国际权势政治秩序(power structure)中的基本态势却首先是激进者,其次是部分激进的改革者,而后是有所选择部分的合作者。这两方面总合起来看,就有着一大基本差异和内在紧张。
无论如何,在目前世界大局势复杂能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国在战略实践中除了坚决阻止和回击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伤害外,首先要“保底”,在“保底”的前提下审慎地积极进取,无论是在“战略军事”还是在“战略经济”方面都须如此。所谓“保底”,就是参照中国悠久政治主流传统中的“战略保守主义”,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我们面前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场一场地打”。鉴于中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变天趋向中可能肆虐的风暴和逆潮?除了上面所说的根本的 “保底”即中国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外,主要有如下三大基本途径或战略。第一,部分地鉴于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时段内疏离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区域的盟国、准盟国和战略伙伴,中国应当坚决确立基本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本着很大的决心和支付必要代价的意识,争取显著改善与美国现有伙伴的关系,争取大幅度地优化中国在东部和东南部周边的战略性外交,舍此,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不会朝积极方向改观。第二,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显著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与此同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将贸易和投资上已持续多年的“走出去”大热潮适当地冷静化,较严格地抑制中国资本过度外流和严重的入不抵出。这对于“一带一路”也是适用的。第三,中国尽管仍要继续建设自己的战略性军事能力,但须改变就此过分地公开宣扬的做法,从而避免军事力量越强则外部反应越大、潜在树敌越严重的“效应彼此抵消”局面。总之,问题涉及中国内外基本方针的较大幅度优化性调整,它们紧迫而又任重道远。
文章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上一篇:周淑真 | 西方主要国家政治选举与政党制度关系分析 下一篇: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