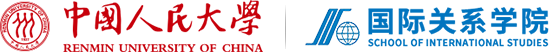来源:人大国关
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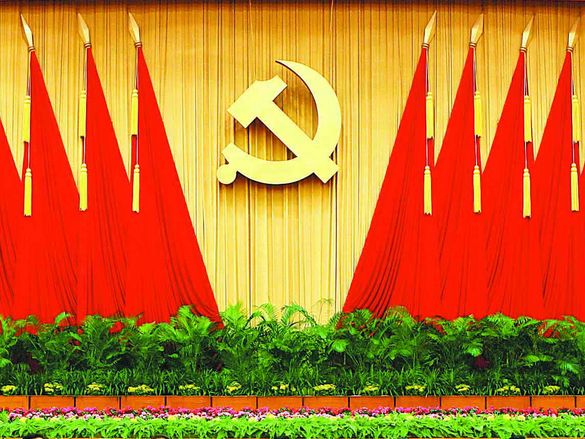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此后经济改革引领社会变革,激发出各领域的活力。伴随经济与社会巨变,政治领域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这40年来中国政治治理发生了何种变化?又如何变化?《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
杨光斌教授的研究集中于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世界政治,他的学术成果不仅在学界影响广泛,也一定程度上作用于政治实践。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之后,政治领域总体而言是在保持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朝着分权化、法治化和更多民主、更多自由的方向发展。他极其看重国家能力,认为国家之间的差别不在政体,而在国家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肯綮,在于形成“有能力的有限政府”。
40年的政治改革方向
南风窗:改革开放40年了,40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带来了何种变化?
杨光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政治的变化。总体方向上,我认为是在保持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这个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朝着分权化、法治化、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我称之为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主义。联邦主义就是权力的分享与共治,地方政府在税收等方面有很大的权力。在国家—社会关系,也就是“官民关系”上,我们有那么多的社团组织,可以说事实上社会有很大的自由。所以总体而言,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地方关系这两个维度上,都朝着更多的民主和自由、朝着分权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
南风窗:这个变化是自发的,还是设计的?
杨光斌:既有自发的,也有设计的。在中央地方关系上,采取分税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过去强调社会管理,后来到社会治理,这些都是设计。有一种说法是经济体制改革一路突飞猛进,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说法,大概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朝着美国的榜样转变,这是一个预设的前提,事实则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参照美国进行改革,结果是怎么样呢?一塌糊涂。
南风窗:你非常重视国家能力,也曾经说过,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政体的差别,而在于国家治理能力。在解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时候,你就用了“有能力的有限政府”这样的表述。
杨光斌:对,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更完整地说就是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制约。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拓展得越来越大,但伴随着市场拓展,权力的手伸得越来越长。郑州市是小麦主产区,人们吃馒头多,所以郑州市专门设有馒头管理办公室;还有的地方管理凉皮、肉夹馍也是类似,老百姓去卖这些东西都需要资质,传统手工艺变成地方政府自赋的一种垄断权力,资格审查通过了才能从事相应行业。这就是政府的手没有边界了。
但是光讲有限政府也不行,有限政府也可能变成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这在西方国家,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还需要国家有能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治理能力的问题。
治理体系其实很简单,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大家都有共识,人民主权、法治、市场、自治,这没问题。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都有这些东西,比如南亚、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他们都有这些所谓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但是它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关键是国家没有能力。印度按照英国体制建立起来了,但它变不成英国,菲律宾按照美国的体制建立,但变不成美国。
南风窗:那如何保障国家有治理能力?
杨光斌:说到底这是一个政治体制、政治机制问题。在中国,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之道,我认为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很多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学中国,但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学不来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民主集中制,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制社会结构就很难改变,国家就无力治理。在我们国家,目前民主集中制正在趋向平衡,当然集中得多一些, 民主的范围可能要小一点。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是,民主得不够,集中得也不够。
中国的民主观
南风窗:你在民主理论方面著述很多,根据你以往的研究,中国人是怎么理解民主的,或者说中国人的民主观是什么样的?
杨光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流行的民主观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有竞争性选举就是民主,没有竞争性选举就不是民主。
所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村民自治研究特别多,成为政治学的“显学”。我的看法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自由多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前并不一定缺民主,中国太大,我也不能说所有的地方不缺民主,而有些地方不缺。比如我所在的村,在我小时候,生产队干部都是选举产生的,不是任命的。但是那时候没自由,上面让你种什么庄稼你就得种什么,这是计划经济。这是改革前后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是按照选举式民主去推进的,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进步,但结果非常不理想。传统的中国农村是个家族社会,宗法在维持着农村社会的和谐。革命以后这个东西没了,改革开放以后有所恢复,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西方选举制度的冲击。在很多村落这种分裂化程度很高,带来的不是和谐而是分裂。
很多人对民主的认识其实非常有限,主要是来源于几个美国作家,比如熊彼特、达尔和萨托利等—就这些可能还没看完。这些人论证的就是选举式民主,往往把民主简单等同于选举。选举民主背后实质上是党争民主。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世界上流行的都是竞争性的选举式民主。但2011年“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这就是选举民主导致的动荡。那发达国家呢?美国出了个特朗普总统,所以美国也从道德高地上走下来了。
因此务实理性的中国人,普遍地开始反思“民主等于选举”这个神话。在学术界也慢慢地开始转向讨论实质性民主,从程序民主转向更多的实质民主。
南风窗:你在谈民主时经常会提到“阿拉伯之春”,它给你何种启发?
杨光斌:政治理论不但来自书本知识,更多的是来源于现实政治,就看有没有能力去捕捉,去观察。我根据这十来年世界政治的变化,总结出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一共三条。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去搞民主,失败是正常的,运转成功是反常的。
第一,是否有国家认同。不能因为搞选举导致国家分裂。事实上很多国家就因为选举导致了国家分裂,南斯拉夫那么小的国家一分为七,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苏联一分为十五。第二,有没有共享信念。即使有国家认同,但一国之内可能“主义”之争特别厉害。且不说不同宗教之间的斗争,哪怕同在伊斯兰教之中,也存在逊尼派和什叶派内部的分裂,结果选举变成了教派斗争的工具。第三,有没有基本的社会平等。因为选票是靠人头说话,所以在泰国肯定就是农民党赢,城市中产阶级必输。
这十来年来,通过学术界关于民主的话语认识,总体来说民主理论正在丰富起来,从单一的自由主义民主,选举式民主,到今天的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还有我提出的民本主义民主,可治理的民主。在学术上,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越来越重。另外,从官方到老百姓,关于民主的认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不再认为美国那一套东西是我们唯一的方向。应该要结合国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南风窗:你提到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在我们国家确实是越来越成熟,它已经为官方层面所认可,这种民主方式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如何体现?
杨光斌: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还有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讲话当中都提到了协商民主,2015年12月份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官方的认定,说明这是一个方向。
中国有协商政治的传统,比如上有古代的廷议,下有祠堂、乡规民约这些东西。但是它衡量起来没有像选举式民主那么简单,选举式民主就是特定时间,到特定地点去投票。
政治是分层次的,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可能就感觉不到协商民主体现在什么地方。就全国层面来说,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协商性质很强,比如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千万人的利益的,有的会通过互联网参与提意见。国务院也规定,凡是涉及到人们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都要有专家认证,相关当事人的协商,这都有例行规定。
第二个层次是部门政策制定。部门政策制定的协商性在加强。比如说滴滴打车的合法化,这个就是协商出来的。三年前交通部门的主管官员带着处长在北大国发院和学者代表、从业代表、企业、官员这四方讨论十几个小时,最后达成共识,滴滴合法化。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太轻市场了,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不过它的决策模式就是这个样子。
第三个层次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很多决策现在都是协商式的,在深圳南山区,几年前,修粤港高速公路,一开始的方案是在地面上修,深圳市老百姓不干,然后政府提出第二个方案,做成下沉式的,老百姓还不干,最后全封闭。这也是协商出来的。
基层政治协商就更不用说了,比如村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这一类。我们的民主体现在特定群体当中,在官员的产生,领导人的产生当中,协商以后有选举程序;但政策过程当中,协商民主是通过协商而达成的共识性民主。所以说要深刻理解中国协商民主需要有对中国的政治分层的理解,分层的解释,不是大而化之地认为有没有。
南风窗:谈民主的时候离不开法治,你的态度是先有法治,而后才有民主,不然民主是没有保障的。
杨光斌:对,西方历史是这样的。什么是好政治?好政治就是民主、权威、法治的动态平衡。人类社会一直走来,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但近代以来,政治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大众民主。民主过多,可能变为民粹,权威过多,也可能变成独裁,因此这些都需要法治去约束。
法治太多也不行。美国的法治主义是什么呢?它在起源上是保护土地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是保护前现代的旧制度的,封建制中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法律最发达,流行的是所谓“法祖宗之法”,所以变法难。亨廷顿在40年前就说,有很多问题产生于法治至上,这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需要政府去推动,但是在美国式的法治主义面前,政府推不动,变成了所谓的“否决型政体”。我们要法治,但是要什么程度的法治?这里面很难有个统一标准,政府要守法,但是不能因此而限制政府去推动现代化。
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民心向背
南风窗:合法性是执政的基石,台湾大学的朱云汉教授主持的亚洲风向标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显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有着很高的信任度和支持度。你认为它可以反映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吗?
杨光斌:我们中国人讲的合法性是民心向背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民意问题。民意如流水,今天支持你明天就反对你,而民心是稳定的。什么是民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稳定的生活,这就叫民心。民意是今天你给我过一条烟,选举时我支持你。有的人不懂民心和民意的区别,民意是不稳定的,要敬畏的是民心。
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学界自己没弄清楚,跟着西方人讲合法性,这会影响我们的自信。西方的合法性讲的是什么?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就没有合法性。换句话说,你的权力不是选举得来的,你就没有合法性。但是合法性讲的不是这个东西,这是1959年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对合法性的改造。
其实最早讲合法性的是韦伯,一个是合法律程序,第二是政府有效。后来李普塞特保留了有效性,把法律程序置换为选举,有选举民主、政府有效才叫合法性。当然这个理论产生以后,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西方乱了,社会失序,从1968年法国5月风暴到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人权运动。发展中国家更乱,政变不断。所以亨廷顿他们开始讨论,不是选举问题,而是治理能力问题,认为政府有能力就是合法性。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讲,西方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自由宪政,而非西方社会的条件完全不一样,因此不能以自由宪政去衡量非西方国家的宪政体制。很多人不清楚这个理论脉络,只知道有选举民主才有合法性,实际上只是关于合法性的一家之言。
弄清楚理论脉络以后就知道,合法性说到底是政府要能提供有效服务,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治理就是一个最好的参考指标。这就是为什么亚洲风向标调查、美国的皮尤调查、北大国情中心的调查都显示,在比较的维度上,老百姓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信任度都是很高的。
所以说合法性这个概念真的需要正本清源,以前我们总是用自由民主来衡量其他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而事实上美国的一些主流学者早就放弃了以那个标准来看待政治合法性。
南风窗: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政绩。
杨光斌:绩效合法性,这个是西方人老在讲的。绩效合法性其实就是有效性,就是说这个政府有效地来给你提供服务,但问题是政府可能不一定总是有效。比如说在地方政治中,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可能反对地方政府,但是不反对中央政府,不反对执政党。所以恐怕也不是说简单的绩效能力问题。
理解这个问题恐怕还得回到中国传统政治关于秩序的看法,天人合一,家国一体。观察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还有这些更大的历史传统。很难用西方的很程序化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中国人讲的是“民心”。
南风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也为全社会凝聚共识提供了一个思想的基础。
杨光斌:对,30年左右更新一代人,新的时代会有很多新的特征、新的挑战性的矛盾,因此就需要新理论、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是要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另外一个是就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要重新解释,重新回答。
新思想当然包括很多了,但我理解,首先它强调历史文明基因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恢复了孔庙,但是官方理论上讲不清楚,也不讲。习近平上任以来,到孔府孔庙,强调传统文化重要性,儒家思想重要性。我们怎么来理解中国,不是40年的中国,也不是70年的中国,而是延续5000年的一个文明体。 要看到文明基因的力量,这个应该首先是很重要的历史哲学。
第二,特别强调人民性。改革开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到十七大、十八大之前,事实上都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换句话说,那可能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强调的人民性怎么体现?体现在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人民主体性,以人民为中心,说到底就是这个。
第三, 是坚持公正的改革原则。过去的改革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效率,但是效率的结果可能引发社会不公正。所以说十八大以来提出,以公正为导向。
最后,是以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这些就是从学术上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内涵。
来源:《南风窗》
上一篇:韩彩珍 | 为什么说外商投资法的颁布将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下一篇:欧树军 | 作为制度的国家:亨廷顿政治视野的整体性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