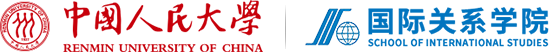来源:人大国关

作者简介
杨光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为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出现于西方思想登陆而中国思想被妖魔化的“转型世代”(1895-1925),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学习乃至移植的产物。其间,先是学习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接着是学习苏联,再接着是改革开放以来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总之一直处于学习之中,各种学说、思潮到今天的量化研究方法,都在学习之列。
中国自己有“国学”而无社会科学,学习是必然之路,否则就没有今天的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文明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也是与西方碰撞的产物。在过去100年里,思想引领实践,实践检验思想,也是外来思想与中国实践相互撞击、相互矛盾、相互调试的“长周期”。
客观地说,作为学科的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国家建设-政治发展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尤其是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混合型”政治体制、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包容了古今中外文明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政治学学科流行的则是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民主与威权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经由此而产生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按照流行的政治学理论而分析中国政治,中国实践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发展,似乎总是不符合教科书中的“标准答案”。
常识是,一个关乎13亿多人口的政治绝对不能迎合任何简单化的理论,要知道没有任何事物比治理大国更为复杂了,这是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同时,基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特定经验而形成的理论也没有资格去鉴定中国政治发展的对与错,我们只能基于中国经验、在比较研究中形成相应的理论和概念。比较研究的发现是,当西方自身陷于困境之中、很多非西方国家也问题重重而导致世界秩序大变革时,中国之路还算顺畅,以至于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替代性模式。
这意味着,中国道路之上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需要一种新政治科学去回答。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上个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委员会自信地宣布,基于老欧洲经验的国家、权力等政治学概念该让让位置了。美国人确实搞出了新政治科学,研究主题上从现代化研究到民主化研究,研究方法上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等实证主义理论。但是,“实证”(the becoming)的逻辑离“实存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being)越来越远,将个人主义本体论弘扬到极致的美国政治学已经陷于危机之中,中国政治学不能把美国政治学的落点当做我们的起点,不能把美国政治学的败相当做我们的榜样。已经学习美国政治学40年的中国政治学,需要有自主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
历史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和人民民主国体与民主集中制政体等新政治学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也是最有力量的“中国学派”,因而解决了中国问题。今天,中国政治学有着特殊的资源禀赋去建设自主性学科体系:第一,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政治学已经足够了解西方政治学,也有足够的包容力去接纳其有益研究成果;第二,和其他学科不同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极为丰富,这是中国自主性政治学建设的最重要的“大传统”和文明基因;第三,有着中国革命经验所形成的“小传统”;第四,有现行民主集中制政体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强大的治理能力和伟大的治理成就;第五,在知识论上,中国政治学直接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一种坚持人民主体性的科学学说;伴随中国走向世界中心而发展起来的比较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规范性学科来源。因为拥有这些如此独特而又优异的资源禀赋,即使在“历史终结论”如日中天之时,中国政治学阵地也没有丢掉。中国政治学理应倍加珍惜并发扬光大这些优质资源,最终形成自主性中国政治学科体系。
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办了《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命运不但系于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赖于国内外同行的鼎力支持。
2018年2月19日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
上一篇:双周论坛 | 我院时殷弘教授主讲“中美贸易对抗的深刻启示” 下一篇:张广生 |《中国政治学》主编寄语:理解政治的知识与技艺,理解世界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