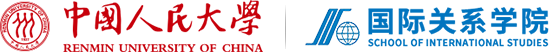来源:人大国关
(徐大同,1928年出生,天津市人,中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华侨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委理事、副会长、顾问,天津市社联副主席、天津市政治学会长、法学会副会长。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现代西方政治思潮》、《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中西政治思想史》;著有多篇专业论文。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问:您能谈谈您与人大的渊源吗?
徐:这次王乐理老师来给我祝寿后带了一本书回去,准备交到学院里,其中第一篇是《我与人大》,写的是我与人大的渊源。我是这样划分的,前三十年是在北京,后三十年是在天津。在北京的三十年几乎又都是在人大度过的。从1949年到1978年,我先后在人大法律系、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所和后来人大停办转入北大国关。
问:那您为什么从法律系转入国政系呢?
徐: 1950年人大刚建校的时候我是在法律系,当时是没有国政系的。1957年反右倾以后,我们干部在1958年轮流下访,当时人大在丰台看丹乡那里有一个农场。我是第二期下访的人员,跟现在人大高放教授在一个队进行基建工作,即盖房子。1960年中央下达命令要建立三个国际政治系,即北大复旦人大。中宣部开会决定,在人大开设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当时国际政治系主任是杨化男,他是原来法律系的主任。但是当时没有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研究方向,我就发挥了法律系的作用,在法律系研究国际与法其实就是政治与法律,杨化男就推荐我去搞西方政治思想史。我们当时劳动期还未满一年,5月份就叫我回来了,所以劳动也就提前结束了,我也没有回到法律系,就直接到了国政系。北大和复旦西方政治思想史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开这门课的。所以人大是第一所开这门课程的学校。
当时人大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是相当大的,由于文革人大停办,到后来慢慢就分散了,有些人去了马列所,后来就剩下4个人,到最后又走了两位,就剩下我和朱一涛,一直拖延到复校,朱一涛在后来还是一直在搞西方政治思想史。
1978年复校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程还是我去上的,像现在国关副院长张小劲、宋新明都是那一届的学生。1979年以后就是朱一涛老师上课了。
在北京的30年中,知识积累主要还是在人大。
我在人大打下了几个基础,一个是马列主义的基础,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包括毛泽东思想。过去讲世界观,现在讲价值论,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另一个是专业基础,在人大开始从事四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直至今夜没有放弃。还有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础。
我一直就当人大是我的母校,在红三楼住了30年。但是由于这两年身体的原因,没怎么到北京去了,人大也就去得少一些了。
问:您为什么离开人大呢?
徐:我离开北京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家属问题。
我跟我爱人分居了20年,当时她在天津我在北京,父母和孩子的户口问题一直很难解决,一直没有在一起工作。现在的年轻人就很不能理解啊!不过现在还可以开车,那个时候就只能坐火车了,很麻烦。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出生后几天才见着面。
1978年复校以后,人大想让我回去,我的关系还是在北大,而北大又想把我留住。可北大又总觉得我迟早要回人大,所以也没怎么管。所以我就决定回天津。
我跟人大作了这样一个约定,人大上课需要我,我还是会来的,所以78级的学生还是我在上课。
不管怎样说,我的成长基本上都是在人大完成的。
问:您是怎样看待人大在在中国的地位的呢?
徐:我一直是把人大当成中国唯一的文科的学校,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问:他们说人大是中央第二党校,您是怎样看呢?
徐:过去是有这种说法。过去人大招生的时候,特别是外交系,几乎都是干部或者是干部子弟。招生时要求8年工龄,想想50年往前推8年,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大多数能来上课的都是干部,出来过后还是干部,所以人们称之为第二党校。
其实人大不是第二党校,而是共产党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跟中央党校也有很大的不同。
问:听说您很喜欢京剧,您对艺术是怎样看待的呢?
徐:我得兴趣很多,京剧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总觉得,一个人不管是干什么的,要培养广泛的兴趣。知识分子要懂点艺术,调剂一下生活,使生活更充实一些,不能只玩笔杆子,变成书呆子;特别是搞文科的,文科的根是社会,不懂社会怎么搞社会科学,懂得社会方式很多,要接触社会的人,社会的事,文艺是一个方面。
在天津师范大学,我搞过政教主任,我就要求政工要会点琴棋书画,寓教于乐嘛!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这也是我现在的看法。
开始对京剧是一种兴趣,由于我父亲就爱好京剧,从小受他的熏陶。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是在两所学校中选择了一所有京剧社的。京剧对我的教育也挺多的,尽管京剧是戏说,但是正戏说对历史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人大京剧团每年都会演出好多场,我唱老生。从解放前到66年一直在唱戏。第一次登台是在天津,最后一次还是在天津。
听说人大现在也有戏剧社,希望一直搞下去。
问:当时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以前从来没有人研究,这是冷门啊?
徐: 没有没有,那时观念跟现在不同了,那时候都是组织分配。要开这门课,就叫你准备。
我原来就是搞国家与法的,所以也不会觉得特别疏远。开始搞西方政治思想,后来苏联专家说要搞特色,不能老讲西方的,所就搞起了比较,由于戏剧的原因,我很喜欢历史,后来又慢慢搞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以说有些时候不是考虑个人兴趣的,搞起来了就不想放下了,个人兴趣在研究中究竟占了多少呢!可能跟本就占不了多少。
问:我们都知道啊,您在2005年出了一套5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您能简短谈谈吗?
徐: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不是说一本书就能讲清楚的。现在有很少是长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有人可以研究一段时间就出一本书,但要出多卷本的书就很困难了,要保罗万象。处多卷本在很早就提出来的,但是过去可以查找的资料不多,很困难。随着后来多了一些研究的人,以及改革开放后翻译过来一些国外的资料,才开始策划。剑桥想出大部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也还没有作好准备。在整个大陆,这是第一部,在全世界也算是比较全的了。多卷本的第二卷是比较有特色的,其他几卷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提炼丰富的。
原来他们想要我出十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那个工程太浩大了,光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问:马上到70周年校庆了,您能来吗?
徐:由于我刚出院,身体不是很好,又赶上他们来给我祝寿,所以还没有决定。到时候看情况吧!
问:您对人大有什么寄语呢?
徐:我只希望人大越办越好,作为真正人民的大学,依然坚持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国家作贡献。
人大从建立开始就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大多数专业是按国家的需要建立的。现在在宣传部门的绝大多数人就是人大毕业的。人大学子也遍布全国各地啊!
虽然我离开人大30年,但是我心里还是记挂着人大,把人大当成我的母校。
上一篇:一起动手捏捏黏土(生活范儿)——《人民日报》专访我院院友张恒君 下一篇:他和毛主席在一起——63级院友蒋含宇访谈录